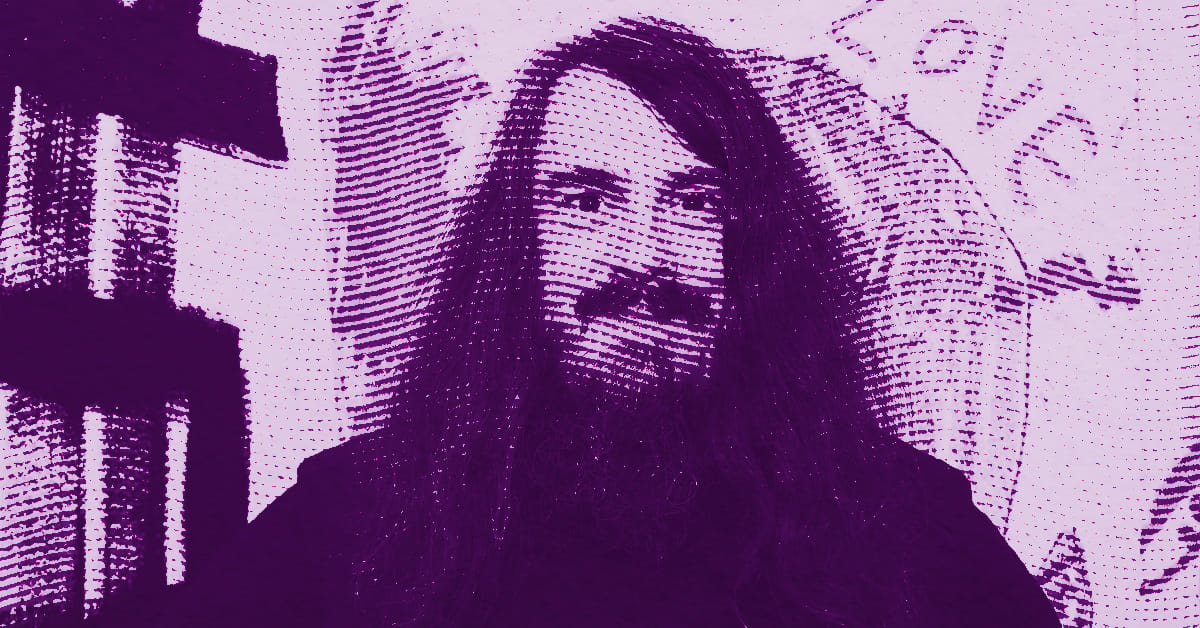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我们面前是当代最令人困惑且必要的艺术现象之一:1970年出生于东京的德国人乔纳森·米泽,二十多年来他以令人钦佩的坚持不懈折磨着我们的审美确定性。在柏林他的堡垒式工作室中,母亲布丽吉特作为创作秩序的严肃教官环绕其侧,米泽创作出一种顽固拒绝被我们常用解读框架驯服的艺术。他的绘画世界充满了被分解的历史人物和被愤怒画笔肆意摧毁的流行文化符号,构成了一种视觉体验,猛烈地挑战我们自身的概念极限。
米泽的作品不仅以一种奢华占领者的随性傲慢占据博物馆空间。它以色彩和形式的暴力呈现其存在,既令人震惊又令人厌恶,营造出一种被困于技术彩色噩梦中且结局始终不可见的特殊感觉。他的画布是真正的战场,色彩颜料与狰狞形象激烈冲突,体现了一种穿透德国艺术史,如炽热刀锋般的表达紧迫感。这种紧迫感根植于复杂的权力、权威关系,尤其是他以狂热传教士般的热忱宣称的”艺术独裁”。
无意识的运作:乔纳森·米泽与精神分析机器
乔纳森·米泽的创作方法展现出与弗洛伊德无意识机制的惊人对应,特别是在将集体创伤转化为绘画材料的能力方面。当代艺术通过抽象或概念作品邀请每个人将自身的体验、恐惧和欲望投射到作品上[1],而米泽将这逻辑推向极致。他的绘画像投影屏幕一样,凝结了我们对于权威、暴力和屈从的最深层焦虑。
这位艺术家发展出一种创作过程,不由自主地令人联想到梦境形成中的凝缩和位移运作。他的历史人物,如希特勒、拿破仑与瓦格纳,经过塑性变形,被剥除历史严肃性,转化为近乎小丑化的滑稽形象。这种象征性贬值操作类似于个体通过心理防御机制中和威胁的方式。米泽并未摧毁这些人物,而是通过过度表现使其荒谬,剥夺了它们幻想中的力量。
他母亲在他的创作过程中那种挥之不去的存在感,是理解他作品精神分析层面的关键元素。布丽吉特·米斯不仅是他的助理,她更体现出一种母性权威,结构化且引导着这位艺术家破坏性冲动的宣泄。这种家庭配置让人联想起弗洛伊德关于升华的分析,即攻击性冲动通过艺术创作找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出口。米斯自己也承认,他的母亲为他的生活和工作室”带来了秩序”,扮演着仁慈的超我角色,使这位艺术家能够赋形于他的执念,而不至于陷入自我毁灭。
米斯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也可从精神分析角度加以明晰。他的”艺术专制”作为一种折衷形成机制,既允许表达全能幻想,又通过其明显的妄想性质使之失效。艺术家将他自身的统治冲动投射到艺术本身,创造了一种理论虚构,从而避免了直接的政治承诺。这种回避策略展现了一种高度复杂的心理结构,能够将焦虑转化为创造能量,同时保持对自身执念的批判距离。
对他的自画像分析亦揭示出一种自我中心的自觉维度,令人联想弗洛伊德关于原始自恋的描述。米斯不断地在他的作品中再现自己,但总是以扭曲、荒诞的面貌,体现出他对自我形象的矛盾态度。这种强迫性的自我表现令人联想到弗洛伊德描述的”Fort-Da”游戏,即儿童通过重复游戏象征性地掌控无法掌控的事物。米斯在他的画作中消失又重新出现,仿佛通过重复他的形象来试图控制自己的存在。
他作品的冲动性维度同样体现在其粗犷的绘画技法中,油漆直接从管中挤压到画布上,避免了传统画笔的介入。这种动作的直接性体现了力比多的直接表达,没有传统艺术实践中的那些升华过程。米斯作画就如同释放紧张感,急切寻求一种无法延迟的缓解。
他对权力男性人物的反复迷恋, , 独裁者、皇帝以及瓦格纳英雄, , 揭示了他对父权权威的痴迷,这些形象既是他认同的对象,也是他解构的元素。这些人物作为象征性父亲的替代,既能被他祭拜,也能被他摧毁,而不必担心真正的后果。精神分析教导我们,艺术可以作为一个过渡空间,演绎我们与权威之间最具冲突的关系,米斯的作品则是观察这些机制原始状态的理想实验场。
瓦格纳与总体艺术品的诱惑
乔纳森·米斯与理查德·瓦格纳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他艺术计划的另一个核心维度:对 Gesamtkunstwerk 的向往,即十九世纪以来德国文化痴迷的综合艺术作品。这种瓦格纳式的雄心深刻影响了米斯的艺术实践,他拒绝局限于单一媒介,同时发展绘画、雕塑、表演、理论写作及歌剧导演。他的多学科方法体现了一种饱和艺术空间的意图,营造出一个让观众沉浸于一致且压迫的整体氛围中。
瓦格纳的影响尤为明显地体现在约翰纳森·米泽的装置艺术的史诗维度中,他将展览空间转变为他个人执念的舞台。正如瓦格纳按照统一的戏剧结构构筑他的歌剧,将音乐、文本、舞台设计和表演融合为独特效果,米泽也将他的展览构想为整体表演,其中每个元素, , 绘画、雕塑、视频和表演, , 都共同参与整体舞台的呈现。这种交响式的当代艺术手法展现了一种造物主般的宏大抱负,不禁令人联想到这位作曲家对文化再生的梦想。
米泽的歌剧创作,尤其是他于2017年维也纳艺术节上首演的《帕西法尔》版本,是这一整体方法的合乎逻辑的顶点。在挑战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时,米泽加入了受拜罗伊特大师遗产困扰的德国艺术家行列。但传统导演往往试图通过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解读来驯服瓦格纳的神话维度,米泽则恰恰将这神话推向最狂放的极致。他的未来主义《帕西法尔》居住着科幻人物,设定在月球基地,激进地强化了瓦格纳的美学,而非使其中和。
这种放大策略展现了他对瓦格纳歌剧美学及意识形态议题的细腻理解。米泽不试图净化瓦格纳的那些争议性面向,而是将其加剧到荒诞,以此创造出一种艺术上的免疫机制,抵御极权诱惑。他的《帕西法尔》成为对集体救赎愿望的讽刺,将神圣的剧目转变为疯狂空间的歌剧,圣杯的探索也变成了B级科幻冒险。
米泽的舞台设计手法也展现了他对瓦格纳视觉符号的娴熟掌握和批判性挪用。服装、布景、灯光借用了拜罗伊特的美学语言,同时被流行和科幻元素”污染”,揭示其人工性。这种风格上的混合制造了一种疏离效果,使观众能看到瓦格纳艺术中吸引力的运作机制,而不至于被其诱惑所俘。
时间维度是瓦格纳与米泽之间的另一交汇点。瓦格纳的歌剧以不寻常的时长展开,其效果淹没观众感知;米泽的装置亦创造出特定且延展的时间感,视觉元素的累积最终导致感官疲劳。这种长时沉浸策略旨在突破观众理性的抵抗,触及更原始、更直观的情感接受层面。
瓦格纳关于文化再生的宏愿在米泽那里得到了当代转译,即他的”艺术专政”理论。正如瓦格纳梦想有一种艺术能够重建德国社会,米泽预言了一个超越传统政治分歧的审美统治时代。这种艺术乌托邦虽狂妄,却体现了德国文化中统合性抱负的持久性,米泽通过极端表述重新激活了这些抱负,同时也通过其夸张剥夺了它们的危险性。
瓦格纳的遗产也体现在米斯对艺术家角色的构想中。正如瓦格纳自视为全面的文化改革者,既是理论家也是创作者,米斯发展了一个繁荣的理论体系,阐述他对世界和艺术的看法。他的宣言、访谈及理论表演都参与了这一教育抱负,使艺术家成为其时代的精神引导者。这种预言式的姿态,继承自德国浪漫主义并由瓦格纳加以强化,在米斯身上得到了当代表达,既揭示了其必要性,也暴露了其局限。
矛盾的美学
乔纳森·米斯(Jonathan Meese)宇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维持看似不相容元素之间紧张关系的能力。一方面,这位五十多岁的男子仍与母亲同住,宣称需要”艺术独裁”,其激烈程度堪比革命演说家。另一方面,他发展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绘画实践,色彩鲜艳、生物形态的形式既唤起童年世界,也暗示成年人的噩梦。这种自觉的精神分裂或许是其审美体系的基石:拒绝任何安慰性的解释,使观众保持在一种富有成效的不确定状态中。
他最近的绘画作品,尤其是那些以斯嘉丽·约翰逊或母性人物为主题的,展现出不逊于艺术史上伟大色彩大师的色彩敏感度。但这种技艺精湛经常被故意粗糙的元素破坏:马克笔文字、随意拼贴、粗犷的堆积,使每幅画都变成美学战场。米斯似乎无法创造美而不立即玷污它,仿佛害怕艺术诱惑的魔咒。
这种自我破坏的美学在他的表演中表现得最为激烈,艺术家在小丑与独裁者、先知与骗子之间交替扮演角色。他的公开亮相总是壮观,制造出一种富有成效的不安,质疑我们对当代艺术家形象的期待。拒绝知识分子的斯文姿态以及浪漫叛逆者的形象,米斯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人格,既荒诞又有魅力,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接受方式。
他与德国历史的关系完美诠释了这种矛盾逻辑。他不回避妥协性的符号,也不直接谴责它们,而是选择通过重复和扭曲将其纳入艺术宇宙,剥夺其戏剧张力。这种象征性消耗策略展现出非凡的战术智慧:通过将邪恶的图标变为彩色木偶,米斯剥夺了它们引发迷恋的力量,同时保留了其批判功能。
他装置中杂乱无章的物品堆积也遵循同样的语义饱和逻辑。玩具、军事文物、流行文化参考、古典作品碎片在有组织的混乱中共存,挑战任何文化层级的尝试。这种过度等同制造出眩晕效应,使我们面对美学价值尺度的武断。在米斯那里,一个达斯·维达面具与拿破仑半身像等值,这种自觉的等价或许是他对当代艺术辩论最具颠覆性的贡献。
超越表象:必要性的问题
在媒体的喧嚣和精心策划的挑衅背后,乔纳森·米斯(Jonathan Meese)的作品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失落幻想的社会中,艺术的必要性。他的”艺术独裁”,尽管带有疯狂的色彩,却表达了一个合理的要求:让艺术重新获得超越文化娱乐或投机投资的社会功能。米斯宣称,唯有艺术能拯救人类免于致命意识形态的侵害,他重新激活了一种贯穿艺术现代史的乌托邦传统,从俄国先锋到法国超现实主义。
这种预言性的维度不应掩盖他形式方法的严谨。米斯对国际当代艺术的规范驾轻就熟,但他选择曲解这些规范,以服务于一个超出常规定义的个人计划。他与阿尔伯特·奥伦(Albert Oehlen)、丹尼尔·里希特(Daniel Richter)和塔尔·R(Tal R)的合作证明了他与同行对话的能力,这与一个沉溺于个人执念的孤立艺术家形象背道而驰。他作品中的集体维度揭示了一种抵抗当代艺术市场极端个人主义的策略。
他近期创作实践的发展,以拒绝为展览旅行和重心回归柏林工作室为特征,显示出值得关注的成熟。在选择定居而非游牧艺术的道路上,米斯强调了创作过程优先于媒介曝光的重要性。这种出人意料的睿智,在一位以过激闻名的艺术家身上,体现了他对当前艺术体系陷阱愈发清醒的认识。
他近期的作品,符号负荷较2000年代的作品减轻,显现出一种相对的安抚感,但不失表现力的强度。以陶瓷面具或精神景观为主题的系列,展现了一位能够演进而不背弃其核心执念的艺术家。这种续新的能力,在当代艺术界少见,暗示米斯可能会摆脱”坏小子”的标签,获得更加持久的认可。
因为归根结底,这正是最关键的:乔纳森·米斯以一种有益的残酷,迫使我们面对自身的极限、恐惧和被压抑的欲望,使得每一次与他的作品的遭遇都成为一次蜕变的体验。在一个艺术景观常受商业需求和体制礼俗所规训的环境中,他保持了艺术那令人不安的功能,迫使我们质疑自己的确定性。为此,带着矛盾的心情,我们应当感谢他。即使,尤其是当他的艺术深刻地让我们感到不安,挑战着我们的界限时。
- “主题、精神分析与当代艺术”, Cairn.info,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