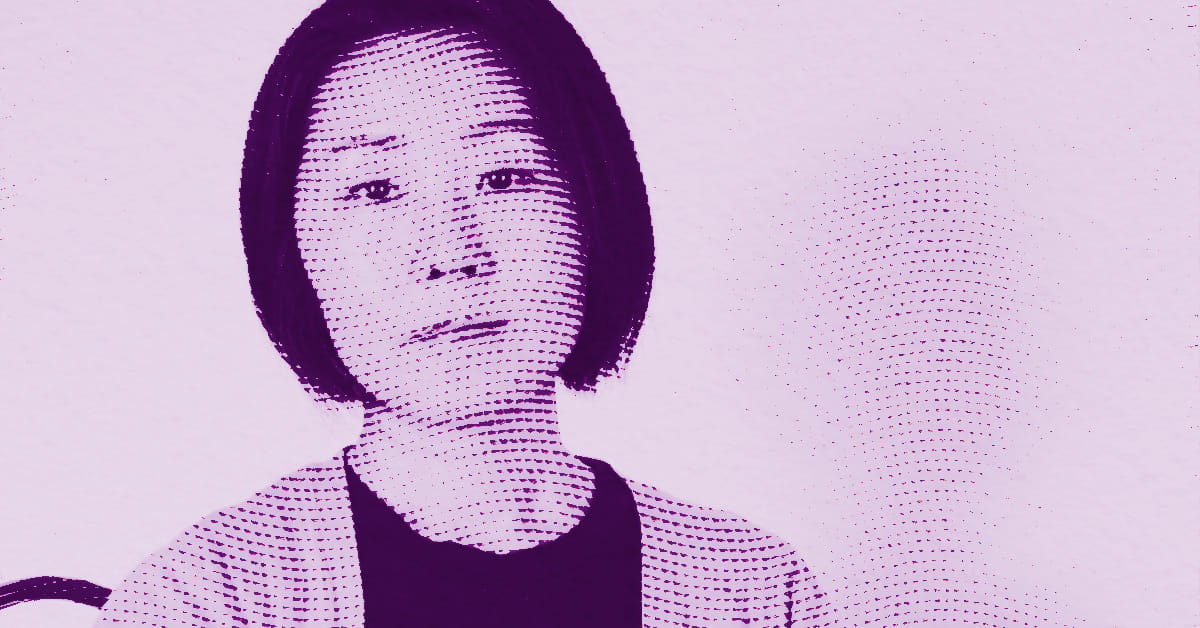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我必须引起你们对关根直子这位日本艺术家的杰出作品的关注,她的创作以无可争议的细腻与深度挑战当代艺术既定惯例,并且在2023年与另外两位获奖者一起荣获了国际艺术殊荣卢森堡艺术奖。
关根是一位矛盾的艺术大师,她轻松驾驭着内在与超越之间的张力,这份随性足以让你们喜爱的概念艺术家嫉妒。她的作品,那些线条交织的闪烁结构,不仅仅是供人沉思的对象,更是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空间与时间关系的装置。
请看《镜像绘画, , 直线与怀旧》(2022年),这件近三米见方的宏伟作品。该作品通过蒙德里安的视角,唤起了纽约城市风景,但关根丽将这一体验推向了更深层次。构成整体的九个不同大小的独立面板创造出物理线条,成为构图的有机组成部分。她像打磨宝石一样打磨石墨表面,将不透明的物质转化为反射面,邀请观众和周围空间融入作品之中。
这种方法让我不禁想起莫里斯·布朗肖关于文学空间的思考,在那里作家消隐于作品背后,呈现出语言的纯粹体验。在《文学空间》(1955年)中,布朗肖写道:”作品将奉献于它的人引向它面临不可能性的那个点”[1]。关根丽在她那镜面般的表面上具体化了这一不可能性的点,营造出图像与现实交融的阈门,使观众同时处于内外之间,彷佛悬浮于令人眩晕的中间地带。
当布朗肖谈论”作品的本质孤独”时,他指向了艺术创造一个自主空间的能力,而这个空间却又仅在与观众的相遇中获得生命。关根丽的作品完美体现了这种张力:它们的反光表面吸收并转化环境,使每一次体验都独特且偶然。她的艺术拒绝固定性,主张感知的永恒运动。
在《堆叠Ⅱ》(2023年)中,关根丽通过并置两类线条, , 由面板拼接而形成的实体线条与手绘线条, , 来玩弄我们的空间感知。这种实物与表现之间的对话让人联想起布朗肖对普通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区分:前者使词汇隐去,只剩意义,后者则使词汇以其物质性显现。
我喜欢关根丽的是她将偶得性融入创作过程的方式。当她提及创作中出现的”意外”,并将其纳入作品元素时,感受到的是一位与材料对话的艺术家,而非强加预设观念。这一做法让人联想到日本侘寂美学,强调不完美与无常的价值。
关根丽从2013年参访的法国史前洞穴中汲取的灵感尤为显著。三万年前那些匿名艺术家们已利用天然壁面凸起来辅助表现动物图案,创造了自然与人类介入的融合。关根丽延续了这一千年传统,将支撑物的物理性纳入最终构图。艺术不再是贴附在中性载体上的单纯表现,而是与世界物质性的协作。
现在谈谈”色彩”系列,关根丽从古斯塔夫·莫罗的《独角兽》和爱德华·蒙克的《柳条椅上的模特》提取色彩调色板,创作出复杂细腻的点彩作品。我感兴趣的并非对这些画家的直接致敬,而是这些作品内在的音乐结构。
这就是关根作品中闪耀的第二个理念:当代极简主义的音乐性。在她的著作中,这位日本女艺术家明确提到了美国作曲家史蒂夫·赖希(Steve Reich)的作品《18人音乐》(Music for 18 Musicians)作为其艺术创作的根本灵感来源。这部于1976年创作的音乐极简主义代表作拥有独特的结构,十八位演奏者和歌唱者集体打造出复杂的声音结构而没有指挥者的引导。这种作曲手法与关根的艺术实践在整体的非层级化理念上产生共鸣:每一个音乐元素(对于关根而言是视觉元素)都保持其自主性,同时共同构成作品的整体协调性。
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谈及赖希的音乐时指出:”这不是开始-中间-结束,而是一种过程,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2]。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关根的作品,特别是她的”Colors”系列,其中每一个精确放置在坐标系统中的色点,营造出超越部分简单叠加的视觉体验。
赖希本人解释说:”作为渐进过程的音乐让我可以专注于声音本身”[3]。 与此类似,关根邀请我们聚焦于纯粹的视觉体验,而非具象或讯息的表达。她的色点制造出类似赖希音乐节拍的视觉振动,这种从相似稍有位移的图案重复中涌现的脉动感。
在《Colors-The Unicorns (383)》(2023年)中,色点形成了关根所称的”循环结构”,其中没有任何元素凌驾于其他之上。就像赖希的音乐中乐器自由进出组合,且无固定层级关系一样,关根的色彩创造了一个互动网络,使观者感知到运动、振动和光学混合,这些在作品实物表面并不存在。作品完成于观众的眼睛与心灵之中,正如赖希的音乐于听者的耳中生动起来。
这种以循环结构对抗传统具象艺术金字塔结构的理念尤为引人注目。关根拒绝所有元素服从于中央图案的设计,偏好一个元素平等互动的星座式结构。这种方法与极简主义过程音乐的层叠渐变相呼应,营造一种令人沉浸的体验,唤起自然循环。
伟大的极简主义作曲家们常说他们不想模仿,只想理解过程[4]。这或许就是关根的座右铭,她不追求忠实再现图像,而是理解并揭示孕育我们世界体验的感知过程。她的”镜像绘画”字面反映了展览环境,使每一次展览成为独特且具情境性的体验。
说到她对日本传统木偶戏文乐的兴趣,又是一次展现了她对那些不同元素(操纵者、说唱者、音乐家)虽保持独立性却共同创造统一体验的系统的迷恋。说唱者和木偶之间的分离、声音和动作之间的分离,形成了一个中间空间,让观众的想象力得以渗透,正如关根的作品中,实体线条和绘画线条创造了一个概念上的缝隙。
《Edge Structure》(2020年)完美地体现了这一方法。在这件作品中,关根沿着抽象图形的轮廓切割,然后从中间取出一个正方形并重新排列元素,创造出新的构图。这种解构与重组的过程让人联想到过程音乐中分解与重构旋律的方式。这位视觉艺术家与作曲家都在探索如何通过转变现有结构来展现新的感知可能。
美国极简音乐以其音乐过程的”可听渐进性”著称[5]。这种过程的透明性在关根的作品中也可见一斑,她不隐藏作品创作的机制,反而将其凸显。面板之间的接缝、打磨痕迹、一层层叠加的材料,所有这些都清晰可见,营造出一种物质的诚实感,直接与观众产生联系。
我喜欢这些平行艺术方法之处在于,它们既能创作出在智力上具有激发性的作品,又在感官上极具吸引力。极简音乐尽管概念严谨,却依然深刻动人、肉体感知。而关根的作品,尽管理论上复杂,却提供了即时且发自内心的视觉体验,那些如镜面般闪烁的表面捕捉光线并改变空间,创造出几乎可触摸的感觉。
《Square Square》(2023年)以错位的长方形和多样的线条类型,创造了一种我称之为”视觉复调”的效果,不同的感知层叠加,却永不完全融合。这种分层让人想起极简音乐中的”相位差”技法:两段略有速度差异的相同图案,逐渐形成复杂的节奏配置。
我已经听见你们低声说:”又是个只为理论家创作艺术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别误会。关根之所以避免了概念上的枯燥,正因她对物质感官性的坚守。那些如镜面般抛光的表面,那些随角度和光线变化的线条,那些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振动的色点,所有这些共同创造出一种即时且超越理性的审美体验。
正是在这里,关根直子的真正原创性得以展现:她有能力调和那些表面上矛盾的方法论。概念与感性、平面与体积、静与动、控制与偶然,在她的作品中共存而不互相抵消。就像当代极简音乐中,数学上的严谨反而产生了一种近乎神秘的冥想体验,关根的作品通过几何的精准,引领我们走向对世界更流动、更直觉的感知。
如果艺术在我们这个充斥着影像的世界中仍有一席之地,那正是它提醒我们,感知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被动记录,而是一种物质性与意识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的积极建构。関根女士的作品通过显现这些感知机制,邀请我们与可见世界展开新的对话,这种对话使我们不再只是观众,而是意义创造的积极参与者。
那么,下次当您看到関根女士的作品时,请停留片刻。观察光线如何在这些抛光表面上跳动,您的倒影如何融入艺术家勾勒的线条,色点如何随距离和视角变化而转变。或许,您会在作品与您的感知之间的无声对话中,听见那些深远的音乐结构的回响,这些节奏性的极简脉动正如我们的心跳,标记着我们生命的时间。
-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Gallimard,1955年。
- 约翰·凯奇,《寂静:讲座与著作》,维斯利安大学出版社,1961年。
- 史蒂夫·赖希,《1965-2000年的音乐著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 史蒂夫·赖希,与乔纳森·科特访谈,《滚石采访》,1987年。
- 史蒂夫·赖希,《音乐作为渐进过程》,收录于《1965-2000年的音乐著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