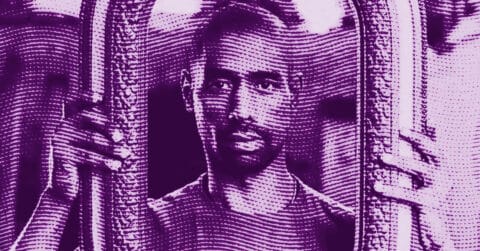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现在是时候谈谈阿尼什·卡普尔(1954年生),这位艺术家近半个世纪以来让我们在狂喜与恼怒之间摇摆。让我告诉你为何这位空间魔术师、感知操控者值得深入关注,尽管你们中的一些人仍更愿意凝视路易十六时代的家庭肖像,说服自己艺术已随着布歇而终结。
阿尼什·卡普尔如同一尊拥有不锈钢双足的巨人伫立,我语气郑重。这位印度父亲与伊拉克犹太母亲的儿子能跻身世界艺术巅峰绝非偶然。但让我们停下脚步,真正探讨他独特的本质,超越艺术市场的惊人数字和汗流浃背的拍卖师。
定义卡普尔作品的首要特征是他对虚无与空间的痴迷。当我说痴迷,不是指某些收藏家对5万欧元新购藏品的执着,那些连自己也未完全理解的藏品。而是一场深刻的哲学追求,令人联想到马丁·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虚无的概念。以芝加哥的”云门”(2006年)为例,那些只懂从美食角度解读的称其为”The Bean(豆子)”。这件100吨抛光钢结构的巨作不仅是喜欢点赞的网红自拍地,更是一场对包含一切的虚无的冥想,是对我们在城市空间中地位的字面及隐喻思考。莫里斯·梅洛-庞蒂见此作或许会爆发颠覆性的顿悟,它完美体现了他的知觉现象学。
当卡普尔创造这些扭曲并淹没空间的反光表面时,他不仅仅是在像一个周日魔术师那样玩弄我们的感官。他迫使我们面对自身对现实的感知,质疑我们自认为了解的环绕世界。在这里,体验是内心的、身体的,无法简化为Instagram上的一张jpeg图像。
他作品的第二个特征,是他对颜色作为物质的革命性运用。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进入了一个让伊夫·克莱因在坟墓中颤抖的领域。卡普尔不满足于仅仅像一位看YouTube教程的周日画家那样将颜色涂在表面。他赋予颜色以形而上的”实体”,近乎神秘的存在。他的单色作品,尤其是使用成为其标志的深红色系列,非一般风格练习,而是加斯东·巴什拉所称”物质-持续时间”的体现,即物质与时间的融合。
以《Svayambh》(2007年)为例,这团红色蜡块缓缓穿行于展览空间,宛如一条血色的利维坦。这件作品不仅仅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表演,尽管它无疑是。它是一场关于时间、变形以及所有创作本质上存在的暴力的冥想。这里的颜色不仅仅是美学属性,它是作品本身,它的肌肤、血液和存在的理由。正如吉尔·德勒兹所称,这是一个”感官块”,一种超越简单再现,成为自主现实的体验。
请不要让我开始讲他对Vantablack的使用,这种材料能吸收99.965%的可见光。当卡普尔获得其艺术使用的独家权利时,有人声称这是颜色的私有化,讥讽是丑闻。然而,这些批评忽略了核心:关键不在于拥有,而在于如何利用。卡普尔的运用创造了视觉深渊,挑战了我们对”看”的理解。就像卡齐米尔·马列维奇拥有了21世纪的技术,他的”白底黑方形”相比之下几乎显得羞涩。
卡普尔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可比拟理查德·塞拉对纪念碑性雕塑的影响,或詹姆斯·特瑞尔对光艺术的贡献。但塞拉强调刚性,特瑞尔点亮空间,而卡普尔则超越了这一切。他的装置不仅置于空间中,更是变换、扭曲、重新创造空间。正如彼得·斯洛特迪克所言,这是一种艺术的”球体论”,对我们存在的空间及我们周围制造的泡沫的探索。
卡普尔创造出抗拒数字复制的体验。在一切即刻可分享、点赞、消费的世界中,他的作品要求身体的在场和直接的对抗。它们提醒我们,艺术不仅仅是屏幕上的图像,而是全身心投入的体验。正如罗兰·巴特所称,这是作品的”刺点”,那个穿透、刺穿并转化我们的细节。
让我们看戈根海姆的《Memory》(2008年)。这件巨型耐候钢装置仿佛同时从博物馆墙壁中拔地而起又陷入其中,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壮举。它是对记忆本身的冥想,关于我们的记忆如何占据心灵空间、如何变形和转化。这是雅克·德里达的三维体现,对空间和感知确信的物理解构。
再来看看他较新的作品,如《Descension》(2014年),那吸引博物馆地板的黑水漩涡。这是乔治·巴塔耶的行动表现,对无形态的具象化,是一种挑战我们分类和整理世界的努力的力量。它不仅仅再现混沌,而是创造、控制并转化为美学体验的艺术。
卡普尔的作品同时在多个层面发挥作用。在直接和内心层面,它们壮观、诱人,无法忽视。但你越是细看,会发现意义层层叠加,与艺术史、哲学、科学产生共鸣。正如特奥多尔·阿多诺所说,这是艺术的谜性特征,即能同时显而易见且难以穿透。
他对材料的运用反映了这种复杂性。抛光钢不仅是一种高科技材料,更是质疑再现本质的手段,正如委拉斯开兹在《宫娥们》中所做的那样,只不过他使用的是21世纪的工具。红色蜡不仅是一种雕塑媒介,更是变革、可变性以及任何创造固有暴力的隐喻。若约瑟夫·博伊斯拥有最新的技术,他或许会这样做。
但别被误导,卡普尔并非这些传统的简单继承者。他重新发明、变革并将其推至极限。当他在巴黎大皇宫创造像《利维坦》(2011)这样超大型且沉浸式的装置时,他不仅仅是在填充空间,更是在重新发明空间。米歇尔·福柯所谓的异托邦,就是存在于日常现实内外的空间。
他与建筑的合作,尤其是在伦敦奥林匹克2012年的阿塞洛尔米塔尔轨道塔(ArcelorMittal Orbit)等项目中,展现了他对雷姆·库哈斯所说的”宏大性”的理解。那是一种建筑变成了其他东西的尺度,超越了简单的功能或美学。这是没有畏惧雄心、不为自己想成为宏伟而道歉的艺术。
或许这正是卡普尔真正重要之处:他能够创造一种不需获得存在许可的艺术。这种艺术并非凭借蛮力而存在,而是凭借其改变我们对世界认知的能力存在。盖·德波称之为对”景观”的挪用,但这是一种并不否认审美愉悦,而是拥抱并超越它的挪用。
所以,的确可以批评卡普尔垄断了Vantablack,批评他某些作品的炫目效果,批评他在艺术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但那将忽视最本质的东西:他是为数不多能够根本改变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当代艺术家之一。这难道不正是艺术的使命吗?
卡普尔提醒我们艺术直接的、身体的体验的重要性。他的作品是对一种不满足于被观看,而必须被体验、感受和实验的艺术的宣言。阿尼什·卡普尔不仅仅是创造非凡物件的艺术家,尽管他以无可比拟的精湛技艺做到这一点。他是使用空间、物质和光线如同他人使用语言的哲学家。他的作品是对我们的感知提出的问题,是对我们理解世界的挑战,是以不同方式观看的邀请。
如果有人执意只将他的作品看作扭曲的镜像和色斑,那就随他们去吧。正如马塞尔·杜尚所说,是观者造就了画作。就卡普尔而言,只有那些真正敢于观看的人,才能在他的作品中发现完整的宇宙。其余的人只能回头去凝视他们的家庭肖像,假装艺术在过去三百年里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