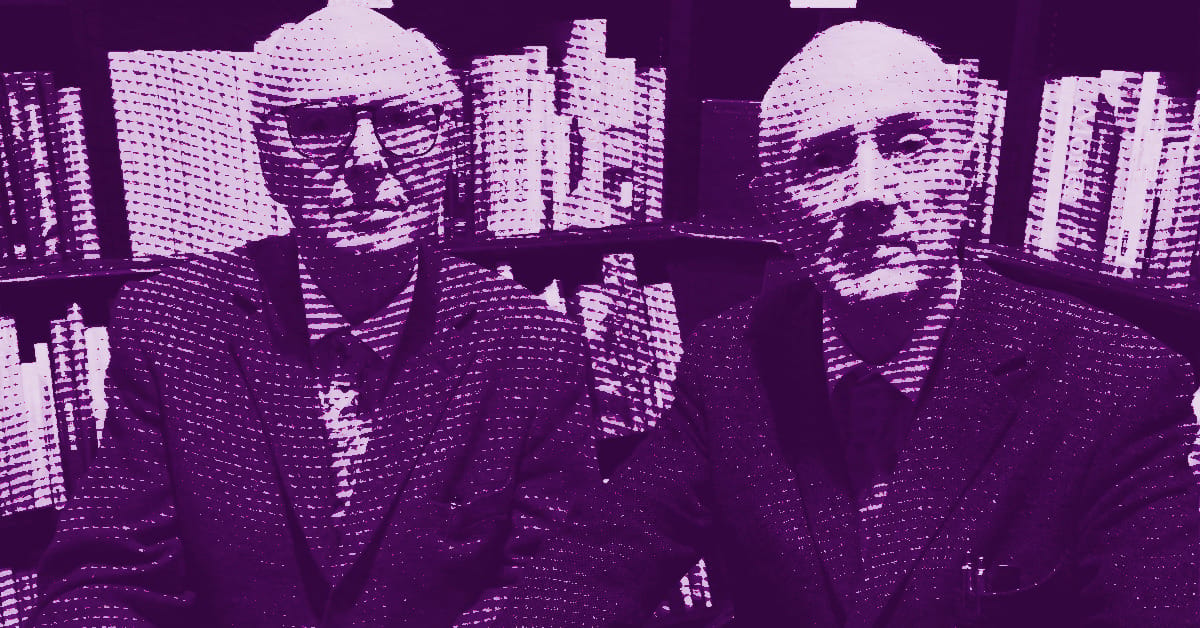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吉尔伯特 & 乔治不是普通的艺术家,试图通过当代艺术史约定俗成的视角来理解他们,将如同仅凭彩色玻璃窗的颜色来评价一座大教堂一样粗浅。这对在1967年圣马丁艺术学院结缘的不可思议组合,系统地构筑出了一部作品,挑战任何匆忙的分类,拒绝被归入某个运动、流派或短暂的潮流。
吉尔伯特·普劳施,1943年生于意大利南蒂罗尔,乔治·帕斯莫尔,1942年生于普利茅斯,半个多世纪以来,二人彰显出的艺术独特性值得我们严谨地关注。他们的创作步调缓慢,几乎如同建筑一般,每件作品都是他们耐心搭建的建筑中的一块砖石。他们作品的建筑性不仅是形象比喻,而是深刻的结构现实。他们自1968年起居住的斯皮塔尔菲尔兹佛尼尔街的乔治亚风格老宅,不仅是一处住所,更是他们艺术实践的熔炉。建筑对他们来说,是语言、方法与哲学。他们对这座建筑的细致修复,恢复原始的装饰,体现了对结构与内容、形式与存在关系的深刻意识。这座房子不是装饰,而是他们艺术身体的延伸,是生活与艺术融合直至难以区分的空间。
自1970年代起构成他们影像拼贴作品结构的黑色格栅,立刻让人联想到中世纪彩色玻璃窗的秩序安排,这些碎片化的组合通过彩色面板讲述神圣故事。但哥特式彩绘玻璃提升灵魂朝向神圣,吉尔伯特 & 乔治的格栅却猛然拉回尘世、肉体,乃至猥亵。他们的《Pictures》系列始于1970年代初,确立了严格的创作体系,每件作品如同一扇伦敦东区的窗户。这种几何结构远非单纯的审美选择,而是在他们几近偏执地记录的城市生活混乱中建立秩序。浓烈且常常刺眼的色彩,被这些黑色栏杆囚禁,制造出压制与爆发、阿波罗式结构与狄俄尼索斯式内容之间的张力。他们作品的建筑结构模仿了城市自身,有窗户、立面、空间划分,组织了人类间的拥挤与亲密。
社会学议题贯穿他们的作品,这一点在经常被指责为轻浮的艺术家中尤为令人惊讶。基尔伯特&乔治不仅满足于观察他们的街区,更将其作为当代社会变迁的实验室。他们声称”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也都发生在东区 [1]”这句话,若没有一系列系统记录该地区社会层面的图像做支撑,或许显得自负。伦敦东区,凭借其移民不断、贫困长期存在及快速绅士化的历史,确实浓缩了西方大都市中的各种紧张状况。艺术家们像身着三件套西装的人类学家一样立足于此,收集现代城市的废弃物:一氧化二氮弹筒、涂鸦、性工作者的招聘广告、耸人听闻的报纸标题。这种积累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一种近乎科学的方法论。从他们身边环境中采集的每一元素,都成为社会阶级、种族、性别关系的症候,揭示了英国社会的结构。
他们对语言的运用,特别是在如2001年的《Ages》系列或2009年的《Jack Freak Pictures》中,展现出对象征性统治机制的深刻理解。通过复刻男性卖淫广告,他们直白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中身体的商品化。收集《Evening Standard》的歇斯底里头条,揭示了煽动恐惧和怨恨的机制,这种情绪滋养了民粹主义。他们作品中反复出现的”Murder””Victim””Gangs”等词,强调了媒体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构造了一个暴力成为社会主要认知方式的现实。基尔伯特&乔治并未显性批判这些机制,其表面呈现的中立态度使其避免说教,但其拼贴作品制造了一种批判性距离感。观众面对的是社会语言的粗粝质感,被截离语境且具体化呈现在艺术作品空间之中。
社会阶级的问题在他们的实践中潜藏贯穿。他们的制服,1969年《The Singing Sculpture》以来一直穿着的过时西装,不仅是审美举动,更是社会学手势。西装在历史上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尊严服饰,是职员、办事员和初级公务员的象征。每天穿着它,基尔伯特&乔治扮演着一种模糊的阶级身份,既非无产阶级,也非贵族,这恰好反映了他们在艺术领域的位置。他们提出”Art for All”(艺术为所有人)[2] 的口号以彰显大众可及性,然而作品却以高价卖给国际收藏家。这种矛盾不代表虚伪,而是当代艺术家处境的真实写照,夹在民主诉求与奢侈品市场之间。斯皮塔尔菲尔兹,他们的街区,也体现了这一矛盾:曾是纺织工人的老工人区,如今却成为伦敦最贵族化的地区之一,乔治亚风格的房屋价值数百万英镑。基尔伯特&乔治在物质与象征层面上都居住在这种矛盾之中。
他们对宗教作为社会制度的处理尤其引人注目。2005年《Sonofagod Pictures》系列作品不仅仅是为了刺激而亵渎。它们反思了宗教事实在世俗化社会中的持久性,以及神圣符号如何继续对集体想象施加影响。通过并置基督教十字架、伊斯兰图案以及他们自己呈现基督姿态的身体,他们突出了宗教的人类学普遍功能,同时揭示了其超越主张的神秘性。宗教显现为众多符号系统中的一种,与广告语言或色情语言一样,既不更合法也不更非法。这种符号系统的普遍等价性,是后现代状况的特征,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特别明确的体现。
种族问题,在他们1980年代和2000年代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带来了艺术家以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挑衅态度所承担的模糊性。像《Paki》这样的标题用以指称一位亚洲男子的肖像,引发了种族主义指控,而他们轻描淡写地以社会镜像的功能回应此类指责。他们辩称自己不是在制造种族主义,而是在记录种族主义。这样的民族志中立立场显然存在问题,因为它掩盖了即使是批判性地复制种族刻板印象也助长了这些刻板印象的流传。然而,他们坚持表现东区的种族多样性,为被边缘化群体提供可视性,也体现了一种包容性,尽管笨拙。他们的最新作品展览于伦敦海沃德画廊,展期至2026年1月11日,继续探讨英国脱欧后社会中贯穿身份断裂线的问题,这一社会他们已持续观察了半个多世纪,令人敬佩地保持了坚持不懈。
盖尔伯特与乔治的艺术行为基本上是将他们自身转化为活体雕塑。这一决定作出于1960年代末,即永不分开露面、始终穿着相同款式的西装、拒绝将工作时间与私人生活时间分开,这种激进令人难以衡量其严苛。他们字面上将自己塑造成纪念碑,成为艺术身份凌驾于个人身份之上的公众形象。这种自我纪念化在2023年盖尔伯特与乔治中心(Gilbert & George Centre)于海尼奇街开幕时达到逻辑顶点,该空间专门用于他们的作品,预示着一个陵墓,艺术家逝世后其记忆将在此保存。因为死亡如今在他们最近的创作中徘徊。2023年《The Corpsing Pictures》系列展示他们躺卧在骨骼上,身着血红色西装。年过八旬之际,他们以同样不矫揉造作的态度直面终结,这种态度贯穿于他们所有主题。
他们对性的态度值得深究。两人在共同生活四十年后,于2008年正式登记结婚,他们的同性关系早在社会普遍接受之前就已成为他们作品的核心元素。1994年的Naked Shit Pictures作品中,他们赤裸裸体,置身于排泄物的图像之中,彰显了人类存在的肉体性、身体性和平凡性。他们拒绝浪漫化的爱情与性的升华,更愿展现其平实的物质形态。这种冷静的视角或显得玩世不恭,但其中也蕴含一种柔情。他们声称他们的作品是”我们向观众发送的一种视觉情书”[3],这表明在挑衅和猥亵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对人类连接的渴望,以及分享无掩饰无虚假的世界体验的意愿。
Gilbert & George的作品难以被轻易归类。作为自称的保守派,撒切尔夫人的崇拜者,支持英国脱欧和君主制,他们颠覆了当代艺术界普遍的进步政治期待。正因如此,他们遭到部分批评家的敌视,后者指责他们纵容反动势力。然而,他们有关法西斯主义和恐同症的作品明确表达了反对压迫的立场。表面上的矛盾其实揭示了二元政治范畴无法完全把握现实复杂性的不足。Gilbert & George跳出了既定框架,这正是他们作品必要性的体现。他们提醒我们,社会生活无法简化为口号,个体非意识形态抽象,而是充满矛盾的有血有肉的人。
他们的遗产远超英国艺术史的范围。他们影响了多代艺术家,从受到他们形象启发而创造机械人美学的Kraftwerk,到在其漫画系列The Filth中模仿他们的Grant Morrison。他们超过五十五年的持续合作本身就是艺术界短暂且追求新颖环境中的非凡成就。他们以修道士般的纪律,逐石逐像地系统构建了一座作品大教堂。这份耐心、对愿景的忠诚及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令人敬佩,尽管其作品某些方面仍可议论。
在对吉尔伯特·乔治(Gilbert & George)艺术世界的探索之旅结束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浮现出来:他们的作品不愿被传统分析框架所驯服。它要求我们用建筑学的工具来理解其结构,用社会学的视角把握其现实根基,用人类学的方法欣赏其文献维度。但它同样要求我们接受其中不可化解的神秘部分,那片晦暗区域里,两个人生融合成一个艺术实体,其内在逻辑必然难以捉摸。他们位于福尔尼尔街(Fournier Street)的家,既是圣殿也是实验室,既是档案馆也是圣所,待他们去世后,将成为寻求揭开这融合秘密者的朝圣之地。但或许这个秘密并不存在,或许吉尔伯特·乔治只是选择了用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艺术,而非仅仅去创作,正是这一原初的决定已经包含了解开他们谜题的全部钥匙。在一个充斥理论话语与概念辩解的时代,他们展示了一种罕见的艺术实践:自我足以,无需翻译或解释,因为它就在那儿,厚重、不可忽视,有时令人恼火,但毋庸置疑地生机勃勃。或许这正是他们最终的胜利:成功地在所有潮流、运动与理论中生存下来,始终坚守本色,两位穿西装的男士从斯毕塔菲尔兹(Spitalfields)街头观望世界的流逝,收集那些碎片,化为光与泥的宏伟教堂。
- 安娜·范·普拉格(Anna van Praagh),”吉尔伯特和乔治:‘玛格丽特·撒切尔为艺术做了很多’”,The Daily Telegraph,2009年7月5日
- 艺术家从早期便采纳的标语,尤见于沃尔夫·亚恩(Wolf Jahn),吉尔伯特和乔治的艺术,或存在的美学(The art of Gilbert & George, or, An aesthetic of existence),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1989年
- 艺术家引述转自《吉尔伯特和乔治在Rivoli震惊》(”Gilbert & George deshock at Rivoli”),ITALY Magazine,2013年1月28日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