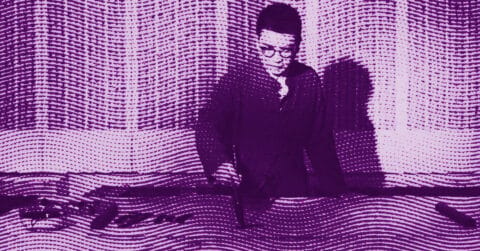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唐纳德·拜施勒从来都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艺术家。几十年来,你们将他归类为”1980年代的新表现主义”,与巴斯奎特和哈林并列,好像这三位纽约人共有相同的艺术关注点。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拜施勒自己反复告诉愿意倾听的人:”我首先是一个抽象艺术家。”然而,我们却持续将他的花朵、圆形头颅和儿童化身视为一种伪装的天真美学,而他却在耐心地构建一部对线条、形状和平衡痴迷的作品。
已经于2022年去世的拜施勒的作品,要求我们按照其自身的条款重新评估。他那些厚重黑线勾勒的大幅画作,背景像当代叠加一样经过处理,超越了那些把它们简单解读为对儿童艺术的挪用的解释。我欣赏拜施勒的是他走钢丝般的能力,正如罗伯特·平克斯-维滕所说的,”在显而易见的香蕉皮和黑暗的香蕉皮之间”[1]。多走一步,作品就会坠入滑稽的矫揉造作。但拜施勒,作为一个老练的走钢丝艺术家,总是在跌落之前停住。
要理解拜施勒,必须首先理解他与艺术史的关系,不是通常归给他的关系(即边缘艺术的传承),而是他自己主张的关系。当被问及其主要影响时,他毫不犹豫地提到了西·汤姆布雷、乔托和劳申伯格。仅此三位!这三位揭示了他的艺术计划的全部:汤姆布雷的原始线条和丰富的表面;乔托的叙事宏大和形式清晰;劳申伯格的拼贴技巧和不同图像并置。
巴克勒对绘画的处理延续了一种美国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他是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现代艺术的重要理论家。这种血缘关系在巴克勒处理简单与复杂、表面自发性与深思熟虑之间的张力时尤其明显。正如马瑟韦尔,巴克勒是一个伪装成直觉画家的知识分子,一个将广博文化隐藏在似乎直截了当的形式背后的学者。马瑟韦尔写道:”现代绘画的核心问题是发现现代结构包含的情感可能性”,这正是巴克勒在他的作品中所探索的[2]。巴克勒与马瑟韦尔的关系围绕着这一共同追求展开:寻找个人表达与绘画形式要求之间的平衡。在他复杂的拼贴作品和表面看似平凡的图像中,巴克勒唤起了马瑟韦尔的精神,后者试图将创作的私人行为转化为公共体验。和他的前辈一样,他操作原型形式(花朵、头部、地球仪)以赋予它们超越表面简单性的情感共鸣。他对高度质感表面的运用呼应了马瑟韦尔对绘画物质品质的关注,即他所称的艺术”本质”。当巴克勒构筑复杂的背景,积累织物、纸张和多层油漆时,他延续了马瑟韦尔将画布视为物质性与概念对抗战场的传统。两位艺术家同样对创作过程本身怀有浓厚兴趣,对所用材料的内在可能性与限制充满好奇。巴克勒喜欢构建崎岖不平的表面,正是为了让他的笔触不至于走得过于流畅,他追求所谓的”内在断裂”, , 一种对绘画动作的物质阻力。这种方法呼应了马瑟韦尔的话:”绘画是在高度紧张状态下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对两位艺术家而言,真实性并非源自无拘无束的表达,而是源自与形式和材料约束的不断对话。如果马瑟韦尔探索纯抽象的表现潜力,巴克勒则游走于具象与抽象之间,利用可识别的形象作为形式探索的借口。他把简单形态置于复杂背景之上的手法,使人联想到马瑟韦尔的《西班牙共和国挽歌》(Élégies à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其中特大型的黑色形态在细腻色彩变化的背景上凸显出来。这种在两位艺术家作品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形象与背景的关系,在巴克勒那里成为一种持续张力的场域, , 介于认同与陌生、亲切与疏离之间。
除了与马瑟韦尔的这种血缘关系之外,唐纳德·贝克勒(Donald Baechler)的作品还与荒诞派戏剧传统,特别是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剧作,保持着引人入胜的对话。这种联系看似令人惊讶,但却生动地阐释了贝克勒的艺术追求。他简化的人物、无根的花朵和漂浮的物体,不由自主地让人联想到充满孤立人物的贝克特式世界,这些人物处于不确定的空间中。在《等待戈多》中,贝克特将人类存在简化到最基本的本质, , 两个流浪汉在一棵枯树下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人[3]。同样,贝克勒将他的题材孤立在模糊的空间里,剥离了所有传统叙事的背景。这种简化与孤立的策略正是两位创作者美学的核心。当贝克特写道”没有什么比不幸更滑稽”时,他表达了一种在贝克勒作品中也能找到的感受,在那里喜剧和悲剧紧密交织。贝克勒简化的人头以其极简且模棱两可的表情,令人想起贝克特人物,他们既滑稽又深沉忧郁。尤其是贝克勒那件名为《Flower》的大型雕塑,展示了一朵风格化、几乎带有漫画意味的花朵,但其庞大的存在感既令人生庆祝之感,也让人想起哀悼,这种矛盾正是贝克特式的。贝克勒作品中特有的时间感也呼应了贝克特的时间观念。在他的画作中,时间似乎被凝结,悬浮在永恒的现在,题材如幻影般漂浮。这种时间的悬置令人生联想到贝克特的剧作,行动仿佛在循环时间中进行,没有进展也无解决。《Walking Figure》是贝克勒在加布雷斯基机场安装的代表性雕塑,描绘了一个不断运动却又似乎静止的身影,完美体现了《终局》中的名言:”事情照常进行”。节约手法是两位艺术家的另一共同特征。贝克特渐进地将写作简化到本质,剔除一切他认为多余的内容,直至晚期作品中达到极致。贝克勒则以类似的方式,将图像提炼为最基本的形态,试图用最简洁的笔触捕捉主题的精髓。这种节制并非冷漠的极简主义,而是通过简约追求最大强度。贝克特的沉默在贝克勒构图的空白空间中找到了绘画上的对应,这些呼吸空间赋予作品显著的张力。两位艺术家都理解,缺席也可以与存在同样富有表现力。重复作为贝克特作品的核心策略(想想《戈多》的循环对话),在贝克勒反复使用相同图案, , 头部、花朵、球体, , 并持续进行无穷变化,似乎是在耗尽它们的可能性或揭示其根本的无意义,找到了对应。最终,贯穿贝克勒作品的独特幽默与贝克特的幽默相似:一种黑色幽默,有时尖刻,源于人类处境的荒诞,以及我们试图在可能毫无意义的世界中寻找意义的绝望尝试。正如贝克特在《无名者》中写道:”我不能继续了,我还要继续”,这句话完美地描述了贝克勒艺术创作核心的生产性张力。
要充分欣赏巴彻勒的作品,必须理解他的工作方法。每幅画作远非自发的举动,而是积累与抹去过程的产物。在他位于曼哈顿的宽敞工作室中,他痴迷地收集图像、照片、报纸剪辑和发现的素描,最终仅保留其中极少部分用于创作。他曾坦言:”在我保存的一千张图片中,可能只用一两张。”这种强迫性积累并非目的本身,而是后续严格选择的必要条件。
使巴彻勒作品如此吸引人正是这种积累与简化、复杂与简单之间的张力。他的背景犹如视觉迷宫,是布料、纸张和绘画层的叠加,而他的形象,那些著名的轮廓、花朵或球体,却异常简洁。这种做法带有某种英雄主义:从当代视觉的混沌中提取出本质的、几近原始的形态。
以1982年作品”Standing Nude (After Shelby Creagh)”为例。这作品展现了一位艺术家,矛盾地努力去忘却绘画技巧。形体粗糙、笨拙,有意显示出不熟练。模特的头部被一个白色云朵截断,激活了形象上方的空白空间。手和脚甚至没有素描,四肢逐渐尖锐细长,或被画纸边缘截断。这一做法标志着巴彻勒风格的转折,介于1981年相对优雅的素描和1983-84年刻意粗糙的作品之间,后者以浓烈的黑线聚合成标志性的、原始的、孩童般的图像,依旧保有极强的表现力。
这种缺乏关节感的表现、拒绝传统写生目标的态度令人震撼。艺术家似乎强迫自己以全新视角观察和感受,或许利用非惯用手绘制。结果是线条更为强劲、坚定,同时也更加粗犷。
这种趋向粗糙和纹理增强的发展贯穿其后续作品。线条成为一个蜿蜒的实体,完美融合了绘画与素描。画面表面呈现出带刺的个性,贴有纸片和撕下的笔记页,增强了媒介的触觉感。拼贴元素同样用作遮盖,抹去部分图像,有时重新构建或修改,有时则留下空白。
许多人曾将这种幼稚、稚嫩的美学解读为简单的风格,实际上这是巴彻勒所称的”内嵌裂痕”的复杂策略。”我的画面是建构出来的,因为我不想知道线条将走向何方,”他解释道。”我希望画笔在画布上的旅程不是顺畅轻松的,我想要过程中出现问题。”
这种粗糙质感的物质性处理在受Shelby Creagh启发的素描中变得尤为突出,适用薄纱布料创造出更粗糙、更密实的表面,使黑色石墨和丙烯线条必须穿行在不断变化的山脊和裂缝的地形中,这是自我设下的障碍,抑制了其早期作品中飞溅般的笔触。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是《Afrikareise》(1984),显然是根据奥地利电影导演Peter Kubelka的先锋纪录片《Unsere Afrikareise》(1966)创作,纪录片跟随一群欧洲白人猎人在非洲的狩猎旅行。尽管电影采用非叙事结构,殖民主义的不平等以及被宠坏的外国剥削者与被剥削的土著居民之间的对比却异常鲜明。
《Afrikareise》中那漂浮在中央、面无表情的苦难之头引发了多种联想,从卡斯特的最后战役以及由此暗示的征服历史和显赫命运的剥夺,到70年代喜剧表演中Steve Martin头戴的幽默箭头。
即便是Baechler的雕塑作品,那些看似直接从他的画布剪裁出来的巨大铜质花卉,也秉承了”内嵌断裂”这一美学理念。《Walking Figure》(2008)是一座9米高的女性铝制轮廓像,矗立在萨福克县机场迎接访客,是完美的例证。她故意做成平面,近乎二维形态,挑战传统雕塑的期待,同时营造出不可忽视的视觉存在感。
促使Donald Baechler成为重要艺术家的,正是他在看似矛盾的世界间游刃有余的能力:抽象与具象、复杂与单纯、幽默与严肃。在一个当代艺术痴迷于新颖和突破的环境中,Baechler构建了一个既微妙对话艺术历史又创造自身视觉神话的作品体系。
请不要误解:Baechler不是一名”涂鸦”艺术家,也非简单怀旧的童年情结者。他是一位严肃画家,专注于追溯现代艺术曙光时期的形式问题。他的作品能使我们微笑,丝毫不减其艺术抱负,反而证明了他对人类处境的深刻理解, , 既悲剧又荒诞。
因此,下次当你面对那些圆形头颅、风格化花朵或标志性地球仪时,请透过表象观看。观察那黑线如何与质感表面搏斗,观察简洁的形象如何从混沌背景中浮现,观察整件作品如何在秩序与混乱、控制与放纵之间摇摆。正是在这种未解的张力中,藏有Donald Baechler的天才。
- Robert Pincus-Witten,《唐纳德·贝克勒》,Artforum,2010年。
- Robert Motherwell,《现代画家的世界》,Dyn,第6期,1944年11月。
- Samuel Beckett,《等待戈多》,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