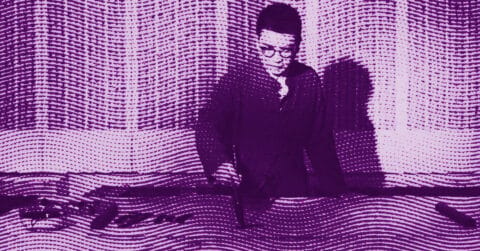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崔洁以城市规划者的外科精度和诗人的忧郁,描绘了中国现代性那漂泊的灵魂。在她那些色彩酸甜的画布上,巨型起重机仿佛拥抱着通信塔,社会主义雕塑与日本代谢主义建筑对话,这位1983年生于上海的艺术家绘制了一幅不断重建帝国的心理地理层叠图景。
她的作品让我们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我们现在都居住在我们建筑乌托邦提前崩塌的废墟中。十多年来,崔洁以远超都市编年史的敏锐,记录并揭示了建筑空间如何塑造我们的主体性,反之亦然。她坦言:”当我画建筑时,我实际上是在画我的情感。”这份简单的话语掩盖了她理论方法的复杂性[1]。
社会空间作为现代性的战场
要理解崔洁作品的意义,必须将其置于法国哲学家亨利·勒费弗(Henri Lefebvre)所发展的概念框架中。这位革命性地改写我们对城市空间理解的哲学家,在其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三部曲及代表作《空间的生产》中论证,空间从不中立:空间既由社会关系生产,又成为这些关系的生产者[2]。空间因此成为政治议题,是权力关系博弈的场域,也是资本主义先进阶段矛盾的结晶。
这一社会学视角与崔洁的创作实践产生了强烈共鸣。她在作品中叠加北京和上海的片段,令一尊苏联雕塑与香港摩天大楼对话,直觉地实现了勒费弗理论中的”差异空间”,这种空间抵抗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她的画作展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建筑风格──从社会主义美学、日本代谢主义借鉴,到西方建筑规范的采纳──在这一分层城市见证中共存,每一层都述说着权力的独特故事。
这位艺术家采用蒙太奇手法,并明确承认奥森·威尔斯是她的主要影响之一。这种电影化的方法使她能够揭示勒费弗所称的”空间的矛盾”:同一地点如何同时承载毛主义集体主义的印记及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诉求。2014年作品《东莞工人文化宫》中,她将典型的苏式文化宫与庆祝科学进步的宏伟雕塑并置,创造出凝聚数十年空间意识形态的复合图像。
这一做法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建筑文档记录的范围。崔洁揭示了中国城市空间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控制装置运作,每一座建筑都承载着政治项目的痕迹。她的作品呈现了勒费布尔所称的”设计空间”,即规划者和技术官僚的空间,同时也展现了”生活空间”,即居民的日常体验空间。当她描绘北京的人行天桥或上海的写字楼时,她捕捉到了公共权力规划的空间与社会使用者所占用空间之间的张力。
崔洁的创新之处在于她能够使石头和钢铁中刻写的意识形态可见。她那些非自然主义的色彩,人工的紫红色、电光橙和合成绿松石色,犹如化学显色剂,揭示了当代建筑的象征性暴力。她展示了中国城市空间远非简单的中性容器,而是积极参与新资本主义主体性形成过程。现代办公楼,拥有幕墙和模块化空间,不仅是工作场所,它还构成了一台制造适应全球化经济要求的新型个体的机器。
文学领地作为抵抗空间
崔洁的创作方法在文学实践中找到了显著的呼应,这尤其体现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中,他围绕着一个虚构的领地, , 山东省高密县,构建了整个作品体系。和这位画家类似,作家通过叠加多重时间性,将官方历史与民间传说、现实与传奇交织,以创造出抵抗文化同质化的叙事空间。
这种方法的相似性并非偶然。莫言和崔洁都属于1978年经济改革后出生的那一代中国艺术家,他们在一个持续变革的世界中成长。他们共同经历了童年景观迅速消失,被标准化现代性取代,抹去了地方特色。面对现代化的这种暴力,他们发展出相似的艺术策略:创造虚构领地,保存对失落空间的记忆。
在莫言笔下,高密成为一个超越传统地理类别的”文学王国”。这个虚构领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的经历,帝制末期、日本占领、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当代变革在这里交织。同样,崔洁的城市景观不对应任何真实城市:它们构成了由不同大都市和不同时代的建筑元素组合而成的复合空间。
这种领地式的方法使两位艺术家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见证,达到了关于当代中国状况的更深层次真理。通过创造浓缩现代经验的虚构空间,他们揭示了领土变革如何深刻改变个体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状态。莫言的”高密王国”和崔洁的”想象城市”作为实验室,试验着人与时间及空间的新关系形式。
山东作家对这一方法进行了理论化,解释说她的文学领域使她能够”审视历史与记忆的动态”。这一表述完全可以适用于崔洁的创作方法,她利用建筑作为媒介,探索中国城市体验的时间层次。当她绘制《Building of Cranes》(2014) 时,在一座通信大楼上叠加了风格化的起重机,她创造了一个叙事空间,不同的现代性观念在其中对话:社会主义美学强调集体符号,而市场经济的消费主义强调个体主义。
崔洁作品中的文学维度同样体现在她营造叙事氛围的能力上。她的画作讲述无人物角色的故事,展现由幽灵般存在居住的空间。这些建筑承载着曾经生活其中的人们的记忆、凝结的希望以及积累的失望。正如莫言在其景观中充满多重且矛盾的声音一样,崔洁的建筑成为多声部的:每个建筑元素都带有自己的声音、叙述和对中国现代性的独特视角。
这种对城市空间的文学化处理使崔洁能够抵制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所特有的纪录性趋势。她不仅仅满足于记录环境变迁,而是重新创造它们,揭示隐藏的层面。她想象中的城市作为批判性乌托邦运作,使我们重新思考与城市现代性的关系。
当代异化的地理学
在她最新的作品中,尤其是2023年展出的”Thermal Landscapes”系列,崔洁将她的方法激进化,引入生态问题。这些新作中,带有反光立面的建筑与表现动物的陶瓷作品相对话,揭示了她对当代城市化环境问题的敏锐意识。艺术家在此探讨了可称为”气候异化地理学”的概念,现代建筑表现为我们与自然世界日益脱节的症状。
这一主题的发展体现了崔洁艺术上的成熟,她成功将对中国城市空间的思考扩展到全球性关怀。她的新作展示了当代摩天大楼以玻璃和钢材立面构成的气候泡沫,它们保护我们免受自然环境影响的同时,又促进其破坏。这一悲剧性的矛盾,即同时被我们的建筑保护又受到威胁,构成了崔洁成功展现的城市现代性的核心悖论之一。
艺术家因此对她所谓的当代建筑的”人工微气候”提出了一种细腻但无情的批判。在她的最新作品中,这些建筑如同技术有机体,吸取环境能量来维持其居民的人工舒适。这一分析与当代生态思想家的关切相契合,后者谴责现代建筑作为环境异化的因素。
但崔洁避免了激进悲观主义的陷阱。她的构图保持了一种根本的模糊性,阻止了任何单一的解读。她融入城市风景中的动物陶瓷并非仅仅作为受威胁自然的简单象征:它们更揭示了生命在我们最人工化环境核心的持久存在。这些源自中国民间工艺的有机存在,见证了一种传统智慧的持续,这种智慧并未被现代化彻底抹去。
崔洁立场的独特性在于她能够保持这种辩证张力却不加以解决。她的绘画使我们面对当代的矛盾,却不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她揭示了我们所面临挑战的广度,同时为乌托邦式的想象保留了空间。这种细腻的态度,既拒绝技术乐观主义,也拒绝生态灾难论,体现了卓越的艺术智慧。
崔洁的艺术由此教导我们如何承载我们的矛盾。面对我们时代的生态与社会紧迫性,她既不提倡对理想化过去的怀旧回归,也不逃避于技术解决主义的未来。她更邀请我们培养一种可以称为”现代性的悲剧意识”的能力:即全然承担我们历史条件的矛盾,同时不放弃超越这些矛盾的希望。
在当代艺术常在装饰性自满与无力愤慨之间摇摆的世界中,崔洁的作品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一种将忧郁转化为创造力的诗意清醒。她的想象建筑提醒我们,艺术依然可以构成社会实验的实验室,是一个发明人类与世界新关系的空间。在这方面,她继承了Art Critic最崇高的传统:将对我们局限的意识转化为对未被思考之物的开放。
- 崔洁,”How I became an artist: Cui Jie”,Art Basel,2025年1月
- 亨利·勒费弗尔,《空间的生产》,Anthropos,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