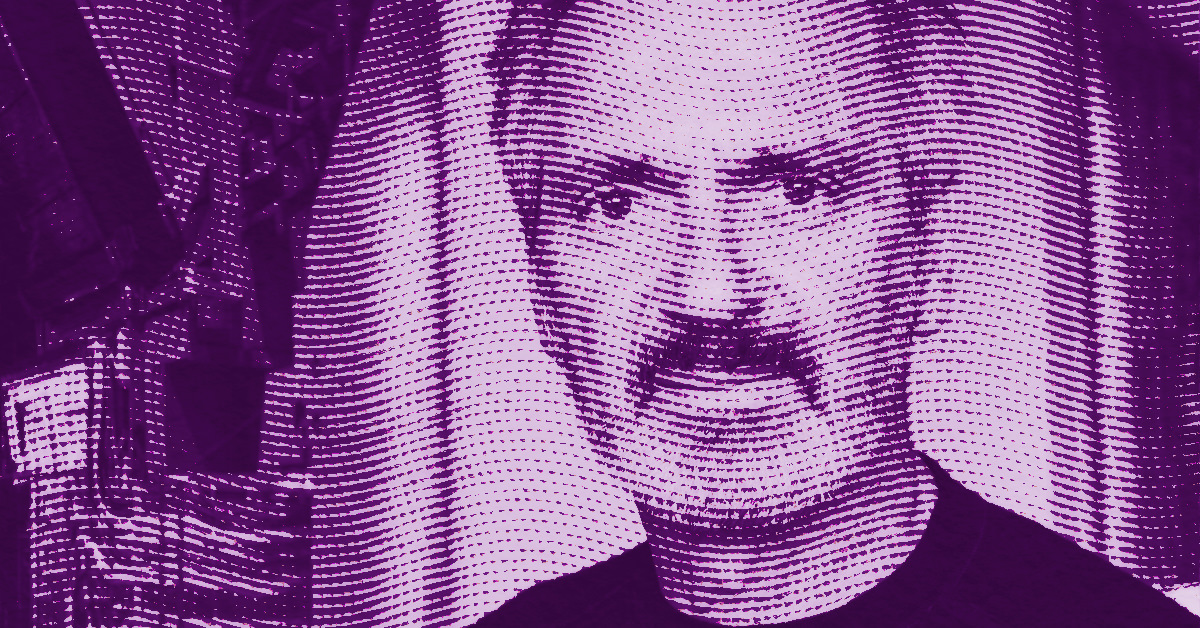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托马斯·斯特鲁斯既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冷漠记录者,也不是被执着描述为贝歇尔继承人的简单继承者。这位71岁的艺术家近五十年来始终展现出一部以无可置疑的连贯性构建的作品,宛如一座当代影像的大教堂,其中每一系列作品都按照严谨如哲学体系的逻辑相互对话。他的相机成为一项对组织我们集体存在结构的持续调查工具,从杜塞尔多夫的空旷街道,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实验室,再到那些令人不安的家庭肖像和博物馆场景,这里演奏着凝视的永恒戏剧。
城市调查
早在1970年代末,斯特鲁斯便发展出一种突破当时传统纪实摄影准则的拍摄方法。他的黑白城市摄影更少展现城市可见表面,而揭示其深层结构,那种组织我们行动和社交的隐藏几何。在《Düsselstrasse, Düsseldorf》(1979)中,艺术家不仅仅记录城市风景,更多地展现了一个社会的时间层叠,公共空间中层层叠加的意图就如地质层理见证地球的漫长历史。
这一方法在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 [1] 的作品中找到了特别共鸣。这位作家形容现代人受”他所创造的对形态”的影响。在《没有特质的人》中,穆齐尔观察到”街道墙壁散发着意识形态”,这一说法似乎就是为斯特鲁斯的城市摄影而写。德国艺术家精准捕捉到这些意识形态的辐射,通过其正面构图和中心视角。每一面立面、每一扇窗户、每一道磨损痕迹都讲述着集体决策、建筑选择以及对现实限制的务实适应。
斯特鲁斯眼中的城市成了一份巨大的见证,叠加了多位历史行动者的意图。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居民、商人、公共当局:他们都在这些被镜头揭示为”无意识之地”的空间留下印记,这些地方凝结了某一时代的力量对比。这种方法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社会学观察,达到真正的当代考古学层面,其中每一细节的建筑都见证了驱动社会体的紧张关系。
这些图像中系统性缺乏人物形象,强化了其作为对结构而非个体进行调查的维度。Struth邀请我们理解建成环境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流动、相遇或隔离的可能性。这些空荡的街道并非无人居住:它们充满了所有曾走过、改变并居住于此的人的幽灵般的存在。摄影师因此揭示了城市空间深刻的政治维度,即建筑框架能够按照超越我们的逻辑引导我们的行为和思想的能力。
家庭肖像
向家庭摄影的转变标志着Struth作品中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这些肖像始于1980年代,与精神分析家Ingo Hartmann合作,探讨了基本社会结构的传递机制。远离传统资产阶级肖像的常规,这些图像揭示了当代家庭动态的复杂性,即组织世代关系的微妙亲疏游戏。
在此处引用Jacques Lacan的理论[2],以全面理解这些构图的意义。这位法国精神分析家展示了家庭如何构成个体符号结构的第一个场所,一个缔结权威关系、性别差异和跨代传承的空间。Struth的肖像正是展现了这些机制在身体的空间组织、目光的分布以及暴露每个家庭配置无意识利益的肢体语言中的作用。
例如,在The Richter Family(1989)中,人物的排列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构图:它描绘了权力关系、默契联盟以及构成这一社会微观世界的情感距离。儿子被父亲抱着,妻子保持的距离,家居空间中物品的布置:每一个细节都组成了Struth镜头以临床精准解读的关系语法。
这些图像如同Lacan所理解的”原始场景”,即个体精神组织凝结的奠基时刻。Struth在拍摄亲人及其家庭时,从不陷入亲密共谋的情绪:他保持着一种分析性的距离,以捕捉这些独特配置中普遍运作的机制。他的肖像揭示了每个家庭如何再现、调整或颠覆源自集体历史的关系模型。
摄影技术本身也参与了这种精神分析方法。较长的曝光时间、需要保持静止姿势、面对镜头的共同等待:所有这些元素营造了一种人工情境,揭示了日常互动流动中常被掩盖的紧张关系。Struth将摄影行为转化为一种揭示装置,能够浮现出组织家庭联系的无意识结构。
艺术家谨慎避免窥视狂的陷阱,保持模特的尊严感。这些家庭严肃地摆出姿势,意识到参与的是超越自身的事业。他们成为更广泛社会配置的代表,使观众能在这些陌生面孔中认出组织自身家庭历史的机制。这种特定的普遍化是该系列的主要审美议题之一,将个人轶事转化为人类学启示。
博物馆摄影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展的博物馆摄影系列,或许是Struth方法中最成熟的成就。这些影像展示了参观者凝视艺术作品的情景,呈现了当代审美体验的复杂性,同时质问了在图像饱和的时代中艺术视角的可能性条件。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II (1990) 是这一方法的完美范例。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女士站在Gustave Caillebotte的Rue de Paris, temps de pluie画作前。她当代的身影与这幅印象派画作中的人物形成共鸣,在城市现代性的两个时代之间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时间对话。Struth因此揭示了过去的艺术如何继续照亮我们的当下,以及我们当代的目光如何反向地转变古老作品的意义。
这些照片呈现出一种令人眩晕的无限镜像逻辑:我们观看着观看作品的观众,而这些作品又表现着正在观看世界的其他人。这层层叠叠的视角展示了艺术体验根本上的反思特质。Struth不仅仅是在记录博物馆的参观过程;他探讨了构成我们集体与艺术及历史关系的机制。
Hans Belting的思想对该系列的影响值得强调。这位德国艺术史学家曾展示图像如何作为”迷宫”,使我们对可视世界理性掌控的尝试迷失其中。Struth的摄影令这一直觉成为现实,揭示了艺术沉思中感知过程的复杂性。每位参观者都带来了自己的故事、参照和期待,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诠释合唱,摄影师的镜头成功捕捉了这种集体的动态。
这些影像的空间布局同样体现了对文化传播政治议题的深入思考。挤满前来观赏La Joconde或Raphaël壁画的游客们,见证了艺术获取的民主化,也显示了其作为消费性表演的转变。Struth谨慎避免简单的批判陷阱:他的作品更多地揭示了审美欲望在塑造当下以注意力经济为特征的时代核心中的持久性。
自然与政治:技术调查
Nature et Politique系列(2008-2015)标志着Struth艺术创作发展的新阶段。这些对科学实验室和技术装置的摄影,揭示了我们技术文明幕后那些通常隐形、编织我们集体未来的空间。艺术家在此以一种综合其前期研究成果的方法,继续对当代结构进行探索。
在Tokamak Asdex Upgrade Periphery (2009)中,Struth使我们面对Max Planck研究所开发的核聚变装置的复杂性。缠绕的电缆、管道和各种设备展示了一个技术世界,这个世界大多超出我们日常理解范围。艺术家不试图解释或普及;相反,他呈现了我们工具的精密程度与我们集体把握其意义能力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这些图像作为我们当代状况的寓言,夹在技术承诺与我们无法掌控其后果之间。Struth揭示了这些装置的塑料美感,同时保持它们的神秘特性。这些实验室成为了我们时代的教堂,是一种技术理性的崇拜场所,声称可以解决人类的生态和能源挑战。
该系列以在柏林莱布尼茨研究所拍摄的动物遗体照片作为令人不安的沉思结尾。这些捕捉到斑马、熊或狐狸安息的图像揭示了在技术永生承诺面前生命的脆弱性。Struth由此建立了一种感人至深的对话,连接我们的普罗米修斯式野心与不变的死亡现实,提醒我们所有政策都受限于自然状况的界限。
整体作品的建筑结构
托马斯·Struth的作品抵御了以独立系列分类的尝试。它更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每组图像根据整体逻辑与其他组交流,逐步揭示其一致性。这种整体结构将每张单独的照片转变为对当代观察与再现条件更广泛研究的一部分。
这种系统方法将Struth置于现代性伟大调查者的传统中,从查尔斯·狄更斯描绘工业伦敦的转变到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绘制都柏林地图。像这些作家一样,这位德国摄影师构建了一个作品世界,能够以结合严密分析与美学敏感度的方法捕捉其时代的深刻变迁。
他在绘画方面的经历对摄影作品这一建筑性构思仍有明显影响。Struth如同画家组织祭坛画元素般构成他的系列:每个面板既拥有自主性,同时又参与超越其个体的整体项目。这种方法让他避免了说明性纪录片的陷阱,达到了真正的当代诗意。
这种构建的特殊时间性很有趣。与媒体时事的逻辑不同,Struth以缓慢节奏开展研究,使他能逐步深化对研究现象的理解。这份耐心体现了他对德国Bildung传统的传承,即通过有理积累经验与知识而渐进形成意识。
Struth的作品展现了当代艺术中罕见的雄心:构建一个能把握当代世界复杂性的再现系统,在不牺牲分析严谨性和美学要求的前提下。这种综合使这位德国摄影家成为理解我们时代变革及其挑战我们集体再现与行动能力的关键创作者之一。
在这个充斥瞬时影像的世界中,托马斯·Struth提醒我们摄影仍可作为认知与启示的工具。他的作品证明,目光的耐心能揭示无形结构,构图的严谨能揭示隐藏的真理,艺术仍可在不放弃其美学维度的前提下,宣称照亮我们的共同处境。这一教训在我们视觉混乱与影像过剩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切题。
- 罗伯特·穆西尔,无特征的人,Seuil出版社,1956-1957年
- 雅克·拉康,著作,Seuil出版社,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