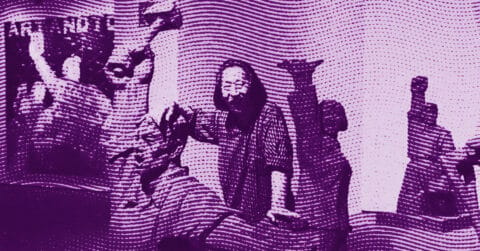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你们自以为全懂当代艺术,拿着那些关于后结构主义解构的自命不凡的讨论吗?但你们真的了解英国帝国勋章骑士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吗?这个穿着荷叶边裙子的骑士,却创造出会让你们那自以为是的笑容消失的艺术作品?
佩里不仅仅是艺术家,更是文化现象,是一场美学地震,震撼了英国艺术界维多利亚时代的根基。出生于1960年的埃塞克斯, , 伦敦知识分子几乎隐藏的蔑视的地区, , 他实现了难以想象的成就:2003年斩获著名的特纳奖,并将陶瓷引入当代艺术的圣地。
佩里之所以卓越,在于他几乎超自然地将尖锐的社会批判编织进作品的本质。他那些经典形状的花瓶,装饰以挑衅性的图像和不敬的文字,正面碰撞了技术精湛与对当代英国社会无妥协的视角。正是这种张力使他的作品如此具有力量。
以他2012年的挂毯系列《The Vanity of Small Differences》为例。受威廉·霍加斯《恶人进程》的启发,佩里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犀利的英国社会流动性探讨。通过这六幅宏伟挂毯,他追踪了虚构角色蒂姆·雷克威尔(Tim Rakewell)的兴衰,他笨拙地穿梭于不同社会阶层。每幅挂毯都是细节丰富的缩影:品牌标志、家居用品、衣物,这些无情定义英国阶级归属的社会符号。
此作令我们想起皮埃尔·布迪厄关于社会区分的观点。法国社会学家展现了我们的审美趣味不仅是个人偏好,而是社会定位的工具[1]。在《区分》(1979年)中,布迪厄阐述我们的文化选择如何强化既有社会等级。佩里巧妙地呈现了这一理论,显示蒂姆·雷克威尔的文化资本随着社会阶层的提升而变化,从折扣超市购物到高级美食晚宴。
“品味就是阶级,划分阶级的是品味”,布迪厄曾如此写道,佩里正向我们精准地展示了这一机制在当代英国社会中的运作方式。这些挂毯揭示了我们对食物、家具、艺术乃至肢体语言的偏好如何成为我们社会地位的标志。正如佩里自己所言:”我关注的是我们如何通过所拥有和消费的东西来标示我们的身份” [2]。
这一本社会学反思并不限于他的挂毯作品。在2011年于大英博物馆展出的装置作品《无名工匠之墓》中,佩里为那些作品充斥博物馆却名字被历史湮灭的无名工匠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致敬。这件作品是对我们赋予艺术与工艺价值的深刻沉思,也反映了这些价值是如何被权力结构所塑造的。
说到权力结构,怎能不提佩里的变装?他的另一个身份克莱尔不仅仅是个怪癖,更是对性别社会建构的挑衅式评论。他以”十九世纪的改革女家长,中产阶级英国的‘再无艺术’抗议者,航空模型制造者,或东欧自由战士”的身份展现克莱尔,颠覆了我们对一位男性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的预期。
这一对性别身份的游戏使人联想到朱迪斯·巴特勒关于性别表演性的理论。在《性别麻烦》(1990)中,巴特勒主张性别非先天本质,而是一种我们不断重复的社会表演 [3]。佩里直观地体现了这一理论,展示了性别如何被建构、解构并重塑。作为克莱尔,他揭示了性别规范的任意性,同时庆祝突破禁忌的愉悦。
但别被误导,佩里并非仅是个试图震惊的挑衅者。他的作品扎根于对艺术史的深刻理解和精湛的技艺。他的陶艺涵盖了从希腊陶器到民间艺术的多种传统,同时坚定地立足于当代。他采用的线圈成型法已有千年历史,而装饰其上的图像和文字则毫无疑问地属于二十一世纪。
这种传统与当代的融合在《沃尔瑟姆斯托挂毯》(2009)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一件长达15米的宏伟作品。该作受拜约挂毯和”人的七个阶段”的启发,描绘了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消费标记轨迹。设计参考了威廉·莫里斯(沃尔瑟姆斯托出生),但制作方式明显现代,先通过数字方式创作,再由电脑控制的织机织造而成。
这幅挂毯让人联想到盖·德波关于”景观社会”的思考。在他1967年的同名著作中,德波批判了消费如何取代了真实的社交关系 [4]。佩里通过展现我们生活中从婴儿尿布到丧葬服务无处不在的品牌和标识,更新了这一批判。这是对现代生活既失落又深刻洞察的呈现,甚至我们最私密的时刻也被商业所媒介。
使佩里如此独特的是他以幽默和易接近的方式探讨这些深刻问题的能力。与许多似乎决定排斥外行观众的当代艺术家不同,佩里积极寻求与广大观众沟通。他的电视纪录片,比如”All In The Best Possible Taste” (2012)或”Grayson Perry’s Big American Road Trip” (2020),是对复杂主题如社会阶级、性别和国家认同的聪明但易懂的探讨。
佩里体现了艺术理论家阿瑟·丹托所说的”艺术终结”,这并非艺术创作的结束,而是定义艺术”应当”是什么的宏大叙事的终结[5]。在一个后历史的世界里,没有任何风格或媒介被优先考虑,佩里自由地汲取各种传统,混合高雅和通俗文化,模糊艺术与手工艺的界限。
这种自由在”A House for Essex”(2015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与建筑事务所FAT的合作。这个房子被设计成一个献给虚构的埃塞克斯女子朱莉·科普的庙宇,是拜占庭礼拜堂到维多利亚时代荒诞建筑影响的大胆融合。它既是一件艺术品,也是一个功能性度假屋,同时对普通生活的抱负和悲剧进行评论。
房子装饰有绿色和白色的陶瓷瓷砖、鲜红色的木工装饰和金色屋顶,色彩的爆炸挑战了建筑美学的传统规范。室内的挂毯讲述了朱莉的故事,”生于1953年被洪水袭击的坎维岛,去年被科尔切斯特的一名咖喱送货员撞倒”。这既荒诞又感人,深刻体现了佩里所有最佳作品的人性。
将这些散漫项目联系起来的是佩里对个人和集体故事的兴趣。像罗兰·巴特(佩里刻意避免引用他,可能因为他在艺术圈过于流行)一样,他理解我们活在文化神话中[6]。但与许多带有冷静疏离态度对待这些神话的观念艺术家不同,佩里以尖锐的同理心对待它们。
以他的童年玩具熊艾伦·米斯尔斯为例。在如”Tomb of the Unknown Craftsman”这类作品中,米斯尔斯呈现为一个神圣的形象,是佩里创造的个人神灵,以在混乱世界中导航。这既感人又滑稽,承认我们都创造自己的神话以赋予生命意义。
对个人故事的关注在”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Girl”(2007)中显而易见,这是佩里与温迪·琼斯合作编写的自传。标题致敬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但内容质朴,讲述了佩里艰难的童年及其作为艺术家和变装者的发展。这是一个超越艺术界共鸣的生存与转变的故事。
佩里的艺术深深扎根于他的个人经历,但它超越自传,涉及普遍关注。他的陶艺充满了对其创伤童年、性幻想和社会观察的引用,同时也更广泛地诉说了人类境况。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为那些不去艺术画廊的人创作艺术。”
这种可及性的意愿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是简单的。相反,它层次丰富,充满历史、文学和流行文化的引用。在《细微差别的虚荣》中,例如,每幅挂毯都呼应一件宗教杰作:”笼中战士的崇拜”让人联想到东方三博士的拜访,而”#哀悼”则指涉西方艺术中无数次对基督的哀悼。
这些引用不仅仅是智力上的暗示,更是将平凡提升为神圣地位的方式。佩里向我们展示,当代生活的仪式,如足球比赛、家庭晚餐、购物出行,都是我们时代中现代版的宗教场景,这些场景曾在几个世纪的西方艺术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这些日常时刻常常饱含消费主义和阶级偏见,它们依然具有尊严。
这种在平凡中寻找美和意义的能力让人联想起米歇尔·德·塞尔托关于日常实践的研究。在《日常的发明》(1980)一书中,塞尔托探讨了普通人如何通过日常活动创造意义,常常是在改造由文化精英强加的结构[7]。佩里做了类似的事情,将普通人的生活和品味提升到艺术的地位。
但佩里并不理想化流行文化。他对工人阶级的偏见和盲点批判同样犀利,如同他对中产阶级的自负或精英的傲慢的批判一样。他的作品揭示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虚伪,包括他如今身处的艺术界。
这种既是内部人又是局外人的矛盾立场赋予了佩里独特的视角。他如今是格雷森爵士,成为体制成员,但仍然对体制的特权和假设保持批判的目光。正如他机智地说:”我早已成为体制成员,也许那些自认是争议人物的人会发现他们如今也已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这种矛盾正是佩里吸引力的核心。在一个艺术界常常在晦涩的精英主义和简单的民粹主义之间分裂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罕见的平衡。他的作品在智力上发人深思,但情感上易懂;技术上精湛,却视觉上即刻引人注目;政治上积极参与,却从不说教。
格雷森·佩里之所以是如此重要的艺术家,是因为他让我们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我们的世界。无论是我们的阶级偏见、性别焦虑还是消费仪式,佩里都向我们展示了塑造我们生活的无形结构。他用幽默、同理心和技术专业的不可抗拒组合完成了这些。
因此,下次你在英国电视上看到穿着荷叶边裙子的男性形象时,请不要换台。因为在假发与荷叶边之下,隐藏着当代最敏锐且最有趣的社会评论家之一。这是一位将陶瓷化为社会讽刺,将挂毯变成阶级评论,并将自己的生活转化为关于身份与真实性沉思的艺术家。在一个模仿者云集的世界里,他是真正的原创。
- 皮埃尔·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午夜出版社,1979年。
- 格雷森·佩里,访谈发表于《卫报》,2021年11月9日。
-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权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劳特利奇出版社,1990年。
- 盖·德波,《景观社会》,布谢/沙斯特尔出版社,1967年。
- 亚瑟·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Seuil出版社,1996年。
- 罗兰·巴特,《神话》,Seuil出版社,1957年。
- 米歇尔·德塞尔托,《日常生活的发明,第一卷:行动的艺术》,加利玛,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