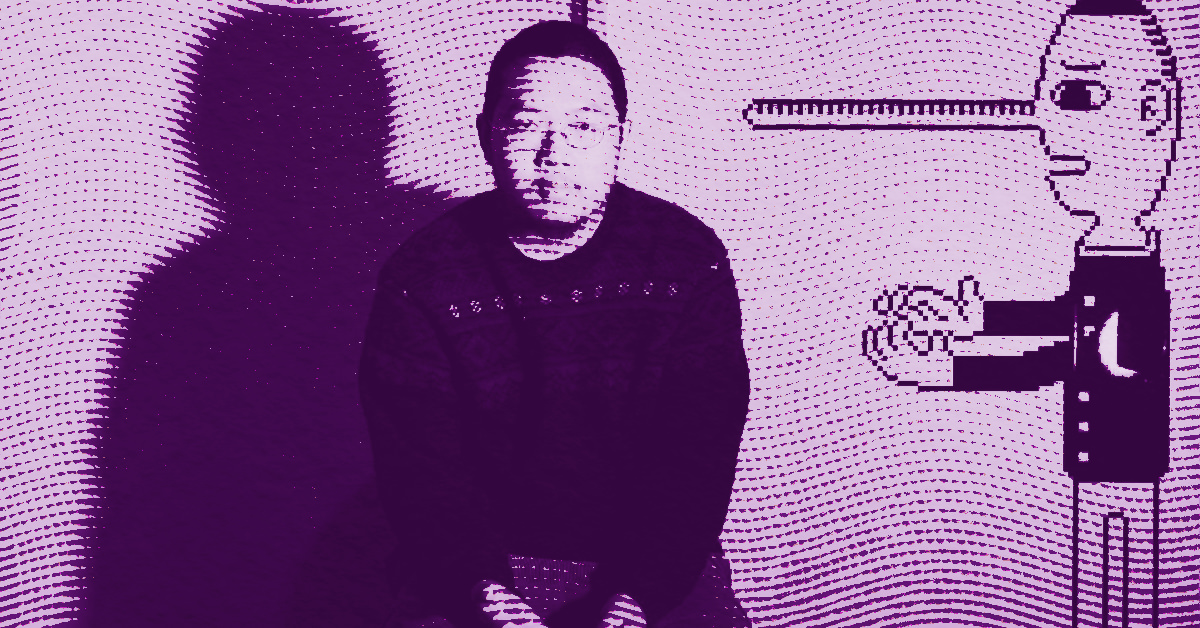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当你们沉醉于西方当代艺术市场的永恒重复时,有人正在中国的工业废墟上画着冒烟的烟囱。烟囱,1983年出生于湖北省,原名彭涵,选择了中文词”烟囱”作为艺名,这个选择对理解他的作品意义非凡。他不断描绘的烟囱,在帝国边缘破败的城乡景观中吐出黑烟,成为他笔下一种严酷之美和衰败美学的象征。
烟囱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专攻中国传统绘画,但他很快放弃传统路径,转向漫画这一在中国仍被视为儿童文学的被轻视媒介。但他的成就在于:他不做普通的漫画。他创作的图像叙事借鉴丙烯画、拼贴、原始艺术及德国表现主义,坚定地拒绝被既定分类限定。由北京Star Gallery和香港Leo Gallery代理,他游走于当代艺术画廊与地下出版物之间,参与博物馆展览和暗地里售卖的复印自制刊物。
烟囱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与德国表现主义意想不到的渊源,这种影响他本人也承认,并特别提到了安克·福赫滕伯格对他创作的决定性影响。这位1963年出生于东柏林的德国艺术家,自1990年代起发展出一种汲取德国表现主义木刻和电影传统的美学。自1997年以来,她在汉堡应用科学大学任教,通过融合各种新叙事技术,重新定义了漫画作为艺术形式的潜力[1]。烟囱坦言:”可能是受安克·福赫滕伯格作品的影响,我开始画头戴动物头的人物。事实上,在看到她的作品之前,我几乎没画过动物……她对我影响巨大!”[2]。
这位中国当代艺术家与德国先锋之间的联系不仅是风格影响那么简单。它揭示了他们在媒介方法和颠覆既定规范意愿上的深层亲缘关系。正如福赫滕伯格和PGH Glühende Zukunft集体利用表现主义木刻美学来与东德新表现主义和国家强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分开来一样,烟囱采用头戴动物头的人物与荒凉工业背景,创造出一种超越传统中国漫画类别的视觉语言。他那些半人半兽的混合生物游荡于分解的城市景观中,废弃工厂和锈蚀的金属结构营造出既非完全现实也非纯粹幻想的氛围。
德国表现主义以其扭曲的人体形象和幽闭恐惧的空间感,一直是社会批判和存在焦虑的艺术表现。诸如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和奥托·迪克斯(Otto Dix)等艺术家,其美学在烟囱的作品中得以延续,他们利用形式上的扭曲揭示了两次大战间德国社会的深层紧张。烟囱虽不盲目模仿,亦承袭这一传统,以记录他个人的现实:一个快速变迁的中国,城乡结合部成为现代与传统、发展与破败之间的无人区。他的布景常常来源于网络,而非直接拍摄,通过这一数字媒介过程,赋予作品一种独特的陌生感。他解释道:”我喜欢这些破败的城乡结合部场景。它们给我一种奇异的新鲜感……当我凝视这些景象时,我总希望某些事情会发生”[2]。
这种对可能在荒芜空间发生之”某事”的期待,或许正是烟囱艺术创作的核心。他的叙述远非传统线性叙事,更像是空间与时间的诗意探索。他的漫画作品既在中国出版,也经意大利Canicola及瑞士Atrabile等欧洲出版社发行,难以轻易归类。它们是自传?还是虚构?界限刻意模糊,艺术家自身也参与演绎,将生活体验与幻想交织。
烟囱对叙事的理解体现了他对漫画作为艺术形式的独特认知。与主导中国市场的日本漫画传统,或塑造西方媒介想象的美国超级英雄不同,他的作品更趋向图像诗歌。他的画板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讲述,而是营造氛围,暗示画面间的情感联系。这一方法呼应其对漫画家工作的描述:”漫画家工作的重要部分,是引导观众穿越作品。”在上海MoCA展出的作品《当你感到沮丧时该做什么》中,他汇集了多段忧郁期创作,将抑郁情绪转化为艺术材质。
这一非传统叙事特质也呈现在他多样化的实践中,他拒绝局限于单一媒介。烟囱虽专注漫画创作,同时涉猎丙烯绘画、拼贴及缝纫。2014年,他受日本艺术家大竹伸朗(Shinro Ohtake)影响,开始进行无预设计的拼贴系列,仅收集并拼接各种素材。两个月内创作约120件作品,这种拼贴实践彰显他不断追求突破创造惰性的探索。如他所述:”我始终寻求探索,并享受失控的感觉,试图避免陷入让人创造旧物的惰性。”
烟囱对艺术市场的立场也揭示了当代中国艺术现场中穿插的特殊紧张关系。作为Special Comix团体的一员,该团体是一部限量印刷1000到2000册的另类漫画选集,他活跃在一个政府审查无处不在的环境中。2014年,他策划了选集”Naked Body”,这是一项直接回应中国印刷出版物中裸体禁令的项目:这是一个公开号召,征集五页漫画,所有主要人物必须赤裸。这一文化抵抗的举动,既具有颠覆性又带有趣味性,展现了中国独立艺术家如何在政治限制与创作自由之间游走。
烟囱代表了这代中国艺术家,他们拒绝将当代艺术与流行文化对立起来。他的原创作品在艺术画廊出售,但他的漫画也在线上、盗版出版物和复印的同人杂志中流传。他既与商业画廊合作,又保持着编辑自主,甚至在退出Special Comix编辑团队后,自创刊物”Narrative Addiction”。这种夹缝中的立场虽然不舒适却富有成效,使他能质疑媒介与流通渠道的界限。
在一次访谈中,烟囱表示他想要”加强漫画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并希望”通过将漫画与画架绘画结合,颠覆公众对漫画的认知”。他补充说:”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漫画不能缺席当代艺术社区,因为我始终认为漫画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尽管大家的观看习惯尚未改变”[3]。
这就是项目的核心:强迫艺术机构承认漫画作为一种合法的当代表达形式,不是放弃媒介的特殊性,而是反而加以肯定。烟囱那些混合型人物、荒凉的工业景观、非线性叙事,并非漫画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妥协,而是同时充分存在于两者领域的作品。这种双重归属感,非但没有削弱他的作品,反而成为其主要力量。
烟囱提醒我们,艺术媒介间的等级制度仍是任意的社会建构,它们反映的更多是我们的文化偏见,而非作品的内在价值。他那冒烟的烟囱、具有人的面孔的动物、废弃的工厂,呈现出一种关于衰败与变革的诗意,远远超出中国国界。在一个当代艺术常陷于自我符号重复、漫画难以走出文化隔离的世界里,烟囱的作品开辟了新的视野。这并非天真地庆祝所谓的跨界融合,而是承认存在能够同时在多种语境中创作且不向任何主流逻辑屈服的艺术家。
教训很简单却意味深长:艺术不取决于载体或流通渠道,而在于艺术家创造出让我们重新思考分类的形式的能力。烟囱在他的北京工作室,继续在我们美学确信的废墟上画着冒烟的烟囱。当你还在犹豫这到底是漫画还是当代艺术时,他已经转向了别的东西。
- 伊丽莎白·奈达姆,《”对我来说,绘画意味着交流”:安克·福希滕伯格及1989年后的德国艺术漫画》,密歇根大学论文,2017年。
- 沃伊塔切夫斯基访谈烟囱,2012年。
- 四喜美术馆,”烟囱 – 概览”,艺术家资料,2025年10月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