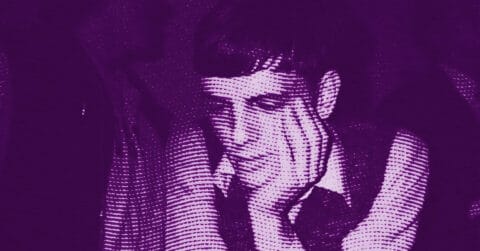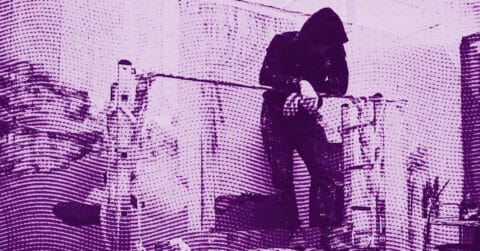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Banksy(1974年生)既不是你们期待的救世主,也不是某些人批判的反基督者。他是一个时代的完美症状,这个时代混淆了信息的简便性与思想的深度,媒体的轰动效应与艺术的相关性。在布里斯托尔的街头和加沙的墙上,他的作品以一种明显的讽刺嘲弄着我们,这讽刺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然而,我忍不住看到我们的当代精神的确切反映,那是一面镜子,照见一个在叛逆与顺从、颠覆欲望与市场服从之间摇摆不定的社会。
让我们从拆解他对权力符号的挪用狂热说起,这自90年代初便构成了他的作品标志。他那些调皮的老鼠充斥着我们的城市空间,不禁让人联想到米歇尔·福柯对权力的概念,那种弥散且无处不在的力量潜入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当Banksy绘制那些装配有相机或监控摄像头的老鼠时,他不仅仅是在创造一幅冲击力十足的图像。他具体表现了本特汉姆的全景监狱理论,该理论被福柯继承,权力通过被观察的可能性行使。监控因此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角,这个社会通过屏幕和镜头的扭曲棱镜审视自身。
但福柯对社会控制机制的复杂性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进行了理论阐述,而Banksy给我们的是预先嚼碎的隐喻,一些强烈冲击但有时偏离目标的震撼图像。比如他的《女孩与气球》于2018年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40万欧元成交后部分自毁。这一举动在构思上很精彩,是对艺术市场的尖锐批评,但又如此刻意,以至于它本身成为了市场营销产品。这场表演奇妙地呼应了盖·德波关于景观社会的理论,即即使是抗议也变成了一种商品。这件被撕碎的作品于2021年以1850万欧元转售,证明了这个系统有无限的能力消化那些声称要摧毁它的东西。
这种根本的矛盾贯穿了Banksy的整个作品,如同一条血红的主线。他在巴勒斯坦的介入,尤其是在隔离墙上的作品,却达到了一种超越单纯挑衅的更深层次的境界。他那些似乎穿透混凝土揭示出天堂景色的错视画作,植根于可追溯到柏拉图洞穴的哲学传统。艺术家字面上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打破幻觉,如何看穿我们构筑的墙壁。这些作品不再是简单的机智表达,而成为质疑我们物理和心理边界本质的抵抗行为。
在这种将艺术作为政治工具的方法中,有一种瓦尔特·本雅明的影子。正如本雅明认为技术复制为艺术的民主化带来了可能,班克西利用模板画固有的可复制性来传播他的讯息。但不同于本雅明所认为的艺术作品光环的终结,班克西反而矛盾地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光环形式, , 短暂性和匿名性。其作品因可能随时被权威抹去,或被不择手段的收藏家”救回”,而显得尤为珍贵。
他的技术本身,模板画,值得关注。简单、高效、可无限复制,使得讯息传播迅速且易于识别。然而,这种技术的简单背后隐藏着概念的复杂性,呼应了雅克·朗西埃关于”感知分配”的思考。班克西选择街头作为画廊,重新定义艺术应出现的空间,打破传统展览场所的等级制度,创造出朗西埃称之为新的”可见性分配”。
这种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张力引领我们进入其作品的第二个核心方面: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对品牌的改造和对广告的讽刺,继承了让·博德里亚关于超真实的分析。当班克西将迪士尼标志变为梦魇般的图像,或将巨大麦当劳叔叔放置于饥饿的孩子旁边时,他不仅制造了强烈的对比,更揭示了博德里亚所说的”拟像”,即传媒和广告构建的现实,最终取代了真实。
他2015年的装置作品”Dismaland”将这一逻辑推向荒谬。这座他自称”不适合儿童的家庭娱乐公园”是对我们休闲社会的精彩解构。通过将预制的幸福符号转变为反乌托邦的噩梦,班克西呼应了赫伯特·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人的分析,即被制造出的人造需求所囚禁的社会。他设计了痛苦抑郁的工作人员戴着米奇耳朵,灰烬般的灰姑娘城堡,载有移民的遥控船,每一个元素都是对马尔库塞所谓”抑制性非升华”的控诉,即系统通过将抗议转化为娱乐来中和反抗。
但问题在于:班克西不断玩弄商品社会的符号,自己也成为了商品。他的作品虽揭露这一体系,却依然以高价在画廊被抢购。这种矛盾不禁让人联想到泰奥多·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批评:即便最激进的反抗,最终也会被它所批判的体系所收编。反叛老鼠的模板画被印制在大型超市售卖的T恤上,抗议图像变成了青少年房间的装饰海报。
Banksy的匿名身份远非某些人所声称的纯粹营销姿态,可以被解读为对这种商业化挪用的一种抵抗尝试。通过拒绝以实体形象代表艺术家本人,他呼应了罗兰·巴特关于作者之死的理论。作品独立于创作者存在,属于观者,属于解读它的人,属于用智能手机拍照记录下它的人,就在作品被擦除或被盗之前。艺术家主动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举动创造了一个自由解释的空间,正如翁贝托·埃科所称的”开放作品”。
他在加沙墙上的作品完美体现了他艺术的政治维度。通过描绘似乎穿透墙壁或借助气球漂浮在墙上方的孩子们,Banksy不仅仅是在创造诗意的图像。他具体化了雅克·朗西埃所称的”异议”,即艺术使不可见的事物得以显现,使被压制的声音被听见的能力。这些介入使得象征压迫的隔离墙成为表达自由与希望的载体。
他关于监控与社会控制的作品同样值得关注。他大量描绘的安全摄像头,经常伴有戏谑或破坏它们的老鼠,呼应了吉尔·德勒兹关于”控制社会”的分析。这些社会继福柯描述的纪律社会之后运行,不再通过禁闭,而是通过持续监控和即时通讯来运作。Banksy在这一主题下的作品不仅是简单的揭露,更提出了抗争的策略,用幽默和讽刺来规避监控。
他与艺术市场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其作品的另一层面。通过在中央公园为几美元组织作品的”野生”销售,及制作本身即为艺术品的真伪证书,Banksy玩弄着艺术世界中价值创造的机制。他的做法呼应了皮埃尔·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分析。谁决定艺术品的价值?这种价值如何被构建和合法化?
他反复使用儿童形象,如拿气球的小女孩、被警察搜查的孩子、投掷花束的年轻示威者,也绝非无意。这是政治艺术传统的一部分,利用纯真作为批判武器,令人想起路易斯·海因20世纪初关于童工的摄影作品。但海因试图记录社会现实,而Banksy创造了寓言,有时对情感的诉诸显得过于刻意。
他的作品中的可复制性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选择模板作为主要技法,Banksy继承了从1968年五月海报到Blek le Rat的传统。但他更进一步,意识地利用数字时代的复制和传播机制。他的作品被设计为供拍摄、分享到社交网络、转换为网络迷因。这种病毒式传播策略呼应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媒体作为人类延伸的分析。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位艺术家,他利用其作品表面上的简洁来传递关于我们时代的复杂信息。他的老鼠、孩子、拥吻的警察,都是社会的镜子,而这个社会往往选择不去面对自己的映像。但过于追求易懂和即时效果,班克斯有时可能会陷入他所批判的陷阱:一个优先考虑视觉冲击而非深层思考的社会。
班克斯的矛盾就在这里:他既是我们娱乐化社会最尖锐的批评者,也是其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立刻被辨识,完美适应社交网络时代,然而它们却声称要批判这种影像文化。他创作的图像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却仍被困在它们所批评的传播方式中。
与其说班克斯是某些人眼中那个颠覆天才,不如说他是我们时代卓越的地震仪。他的作品以简单的讯息和高效的执行,完美反映了一个在叛逆欲望与顺从娱乐的社会之间摇摆的社会。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他已成为展示叛乱如何沦为商品的艺术家。这或许是他最大的成功:让我们看清这种矛盾,尽管他本人也未能避免这些陷阱。在一个真实性成为最珍贵的赝品的世界里,班克斯仍是终极的幻术师,既揭示操控的幕后,又娴熟操纵其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