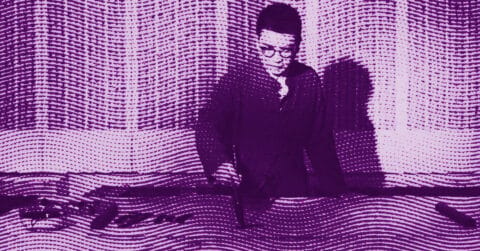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当你们沉醉于观念艺术和短暂潮流时,有位在首尔的女性正在复兴你们选择遗忘的事物。朴英珠不只是绘画风景,她是在唤醒灵魂。这位1970年出生的韩国女艺术家直接在揉皱的韩纸上塑造出现代文明埋葬于混凝土与钢铁下的人性最后见证。她那些棚户区村庄,那些黑暗中灯火通明的贫民窟,不仅是怀旧的象征,更是一种诗意的抗争,回应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称的”后现代状态” [1]。
在1979年发表的《后现代状态》中,这位法国哲学家诊断了构建西方社会的宏大叙事的终结。再无统一的神话,再无集体解放的计划,只有散乱的意义碎片和难以赋予世界连贯性的”微叙事”。这一定义形成于发达社会信息化萌芽时期,至今在朴英珠的作品中产生了令人惊异的呼应。她的画作正绽放于利奥塔预见的这片荒芜之地:那里,旧有的进步与城市发展的叙事已让位于无数脆弱的个人命运,它们在注定被拆除的棚户窗前闪耀。
这位艺术家并不掩饰其灵感的自传背景。她出生于首尔的贫民区,那里正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韩国经济扩张期间系统性拆除的棚户村。她在巴黎美术学院受训,法国赋予她思考自身境遇的观念工具,随后带着流亡者的新视角回到故乡。当她登上南山俯瞰暮色中的首尔,这些黑暗中闪烁的灯光呈现出史诗般的意义。每一点光芒述说着一个生命,每一幢倾斜的房屋承载着看不见的居住者的梦想与绝望。
这种全景式视角绝非偶然。它继承了普鲁斯特式的传统,声称无意识的记忆能揭示时间和存在的真实本质。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精彩地展示了一个简单的感官细节, , 蘸着茶的玛德琳蛋糕的味道, , 如何打开记忆之门,重现整个时代的最细腻复杂 [2]。在朴英珠的作品中,正是韩纸那粗糙的质地,这种以桑树皮制成的传统韩国材料,扮演了记忆触发器的角色。通过揉皱、撕裂、揉搓再将纸张粘贴到画布上,艺术家不止于一项技艺,而是在完成一种复苏的仪式。
郑永珠的创作过程值得细细品味,因为它展现了深深扎根于韩国文化的艺术哲学。韩纸绝非偶然被选中,这种千年古纸,传统上用来铺贴房屋内部,具有独特的光线吸收和热调节特性。她将其作为城市绘画的原材料,在象征意义上连接了传统居所与她所描绘的当代贫民窟。她在将纸张贴于画布前所施加的折皱,模拟了纸张的老化与时间的磨损,同时也体现出历经世纪洗礼材料的韧性。这种近乎雕塑般的触感维度,使每件作品都成为绘画与浮雕、二维与三维交融的混合体。
普鲁斯特的影响不仅限于创作过程中的感官层面。它深入到郑永珠对艺术与时间本质的理解。正如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者晚迟地发现,只有写作能够拯救时间免于遗忘,这位韩国艺术家也明白,她的画作是抵御这些脆弱世界被有计划消逝的唯一屏障。马塞尔·普鲁斯特曾写道:”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的天堂”。对郑永珠来说,自2008年以来不断描绘的这些临时村庄正是这层意思:一个必须从遗忘中拯救出来的失落世界,不是出于无谓的怀旧,而是因为其中蕴含了现代胜利主义趋势中易被践踏的重要价值。这场韩国版的”寻找失去的时光”通过极具情感张力的绘画动作得以实现。
她的作品不仅仅是记录这些贫民区的消失。郑永珠的作品对城市贫困进行了真正的诗意变形。她的夜景构图被一种似乎从临时住所内部散发出的金色光辉浸润,赋予了这些脆弱建筑以前所未有的尊严。波纹铁皮屋顶、裸露的砌块墙、盘旋于房屋之间的歪斜楼梯, , 众多被官方城市规划视为疣痕须被剔除的景象,在她的笔触下获得了忧郁的美感,让人联想起普鲁斯特关于孔布雷的山楂树或维沃纳的睡莲的最美篇章。
这对贫困的审美化若没有明确的政治视角支持,或许会显得令人怀疑。郑永珠毫不掩饰,她的画作是一种对这些草根社区被有计划抹除的抵抗。在已成为亚洲最发达经济体之一的韩国,这些贫困地带的存在令人深思。她避免把问题简单化, , 她不妖魔化城市进步,而是让那些趋向被掩盖的部分显现出来。她的作品成为韩国”奇迹”官方叙述中必不可少的反向镜头。
这正是对利奥塔(Lyotard)引用的全部相关性的体现。这位法国哲学家在后现代条件下指出了他所称之为”元叙事”的终结, , 那些赋予集体历史意义的宏大叙事。进步的叙事、科学与技术解放的叙事、不可避免走向更好世界的叙事,所有这些随着20世纪的灾难而崩溃。在这种”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利奥塔主张重估”小叙事”,即那些地方性、独特的故事,摆脱宏大叙事的极权逻辑。郑永珠(Joung Young-Ju)的作品完全符合这一视角。面对韩国城市发展的元叙事,她以那些点缀其画作的点亮的窗户,反映了无数个体的微型叙事。
但这位艺术家在对当代条件的思考上比利奥塔更进一步。在哲学家仅仅承认意义的碎片化时,她提出了一种诗意重组的形式。她的城市景观虽然表现了脆弱的空间,却散发出令人不安的宁静。这种表面的平静绝非无奈,而是一种与人类条件脆弱性的和解形式。她拒绝将作品中的居民抹去(不同于以往的说法,人类形象是存在的,但内化了,仅通过这些家居光亮得以感知),郑永珠暗示,一个社会真正的财富不在于其摩天大楼,而在于其保存普通人类空间的能力。
这种平凡哲学扎根于一种特别的亚洲感性,值得强调。与倾向于戏剧化或英雄化题材的西方艺术不同,郑永珠的绘画培养了一种沉思的谦逊,令人联想到禅宗美学的最成功之作。她的构图始终遵循重复与变化的原则,建立了一种视觉节奏,邀请沉思而非分析。人们会想到那些每块石头、每撮苔藓、每片叶子都参与和谐整体而不失自身独特性的日本庭园。同样,郑永珠画作中的每座房屋既作为整体的元素存在,也作为承载自身历史的个体微观世界。
这一沉思维度不应掩盖艺术家的技艺精湛。她对韩纸(hanji)的运用显示出对物质与质感效果的熟练掌控。通过叠加揉皱的纸层,然后涂抹丙烯,她创造了细腻的浮雕,光线在其表面意外地反射。自巴黎学习期间以来发展出的这一技法,使她获得了罕见细腻的深度和色彩振动效果。赭石、棕色、金色在这些不规则表面相互交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色域,既唤起时间的铜绿,也呼应了家庭炉火的温暖。
钟容珠最近的作品发展证实了这种方法的正确性。她最近的作品,尤其是在2024年底伦敦Almine Rech画廊展出的作品,体现了她在艺术探索上的深化。画作的尺寸变大了,构图变得更加复杂,但最重要的是,光线在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穿透城市黑暗的金色光辉,不仅仅表示有人存在,更似乎蕴含着一种普遍的希望。她本人也承认:”光线更加大胆地向外散发,照亮得更广泛。”
这种光明主义的演变可以被看作是对当代地缘政治剧变的艺术回应。在亚洲大都市崛起为世界新中心的时代,首尔与东京和香港竞争彰显现代性的胜利,钟容珠的作品提醒我们,这种经济成功不能让人忘记其背后的人文基础。她所描绘的灯火通明的贫民窟如同城市的死亡提醒(memento mori):它们提醒我们,所有的伟大都建立在脆弱之上,而真正的艺术使命是保持这段记忆的鲜活。
正是基于这个意义,钟容珠的作品远远超越了其韩国的语境,获得了普遍性的维度。正如一位评论家在她伦敦展览时所指出的,”世界上的每个大城市都有它的贫民窟,无论是里约的贫民窟(favelas)、伊斯坦布尔的gecekondu,还是底特律的棚户区(slums)”。通过聚焦这些边缘空间,艺术家触及了当代城市生活中一个本质的层面。她对模糊屋顶的拼贴作品象征着世界上其他所有的贫民窟,揭示了跨越文化差异的人类共同存在。
这种普遍主义维度并不妨碍作品深深扎根于其特定的文化语境。韩纸的使用、对首尔郊区”달동네”(月亮村)的不断引用,以及受韩国落日色调启发的色彩调色板,这些元素都牢牢地将钟容珠的绘画作品植根于特定的地理和文化之中。正是这种成功地将本土与普遍结合的方式,使她的作品具有强大的艺术冲击力。通过极致雕琢她的韩国小天地,她得以表达关于人类境况的根本性主题。
还必须强调作品中渗透的精神层面,几乎可以说是神秘主义的。钟容珠并不掩饰:她的天主教背景深刻影响了她的世界观。虽然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徒,仍然保持着对”永恒与精神力量”的坚定信仰。这种超越性的维度为她的绘画注入了一种特殊的光芒。她笔下的夜村沐浴在一种不仅是物理的,更是形而上的光辉中。从中可以辨识出她对绝对的追求,这让人联想到普鲁斯特关于艺术作为启示更高真理的最美篇章。
这种精神追求也体现在艺术家对无限的独特理解中。与大多数明确界定其构图的风景画家不同,郑永珠总是让她的村庄超出画布的边界。”我不喜欢有终点,”她解释说。”我希望我绘画的世界是永恒的,因此我甚至在远处画房屋和灯光。”这种无限的美学使得每一件作品都成为更广阔宇宙的碎片,是通向看似无限延伸的城市宇宙的窗户。观众因此被邀请在脑海中继续超出画框边缘的景观,想象这些小巷和屋顶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
关于这种艺术探索的未来,我们仍需深思。在经历了城市化转型的韩国南部,当最后的贫民窟被拆除后,这种关于脆弱生命的绘画将何去何从?艺术家本人似乎已经预见了这个问题。她最近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自然元素,例如光秃的树木和山丘,或许预示着她将向不那么专注于都市景观的方向发展。她坦言:”我计划画一幅包含自然的景色,并怀着自然也会消失的想法,就像我的故乡正在消失一样。”这种主题的拓展体现出她的生态意识,进一步扩大了她艺术信息的影响力。
正是这种能力,使得郑永珠的伟大得以显现:她能将看似琐碎的主题, , 首尔贫民区的消逝,转变为对人类脆弱性普遍反思的冥想。她的画作如同城市哀歌,讴歌着我们时代所执着摧毁的隐藏之美。因此,她的作品继承了艺术作为对纯粹实用性统治的诗意抗争的伟大传统。它们提醒我们每一扇亮着灯的窗户背后都隐藏着不可替代的宇宙,而文明的真正财富在于保护这些受威胁宇宙的能力。在一个金融逻辑趋向于一切同质化的世界中,郑永珠的作品构筑了一座独特与人性的堡垒,应当受到赞颂。
- Jean-François Lyotard,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巴黎,Éditions de Minuit,1979年
-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巴黎,Gallimard,1913-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