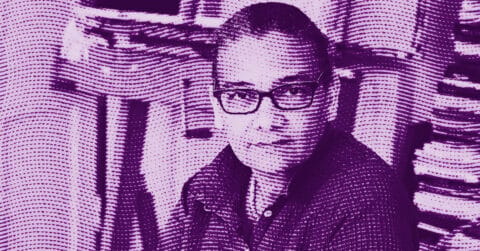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当你们为巨幅画作和喧嚣安装惊叹时,艾莉森·诺尔斯用了六十年时间创作一部极其低调的激进作品,几乎变得隐形。这位上个月逝世的美国艺术家,是Fluxus的创始人物,她将日常变成乐谱,将豆子变成乐器,将沙拉变成诗意事件。她的艺术遗产不以惊人之举衡量,而在于重复的动作、细致的关怀和共享的存在感。
1933年出生于纽约的艾莉森·诺尔斯,最初在普拉特学院研习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师从阿道夫·戈特利布和约瑟夫·阿尔伯斯。但她很快意识到了后来用令人无比清醒的话语表达的道理:”在那里我学到的是我是个艺术家,但我本该学到的是我不是一个画家”[1]。这一觉醒促使她在兄弟家的后院举行篝火焚烧,毁掉所有画作,这一开场白预示着她进入先锋Fluxus运动的世界。1962年,她在德国威斯巴登参加首届Fluxus节,与乔治·马西乌纳斯、派克南俊和迪克·希金斯并肩,这位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
乐谱作为动作诗歌
艾莉森·诺尔斯对20世纪诗歌史的贡献仍被严重低估,可能因为她的实践拒绝传统韵文的装饰,转而采用Fluxus所称的”事件乐谱”(event scores)形式。这些文字极其简短,构成行动协议而非封闭的作品。诺尔斯自述它们是”一两行内的行动食谱”[2]。表面上的简单定义掩盖了概念上的巨大复杂性。
以1962年在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创作的《做沙拉》(Make a Salad)为例。乐谱仅有三个字:”做沙拉”。然而,这条简洁的指令产生了感官和社会层面极为丰富的表演。艺术家伴随现场音乐切菜,用麦克风放大切割声,将食材抛向空中混合,然后为观众提供沙拉。几十年来,此作品不断变形:2008年在泰特现代美术馆,诺尔斯为1900人准备沙拉,使用耙子搅拌,铲子分发。作品成长、转变,却始终保持其本质:将家务动作提升为集体仪式。
Knowles的诗学属于欧洲具体诗歌的一个独特脉络,同时因其对身体和触觉的关注而与之区别开来。具体诗歌在页面上处理语言的物质性,而Knowles将其置于表演的空间与时间中。她的乐谱并非供人凝视的作品,而是体验的邀约。1969年开始的《The Identical Lunch》便体现了这种方法:艺术家每天吃同样的饭菜,”一份金枪鱼三明治,配烤小麦面包、生菜和黄油,不加蛋黄酱,以及一杯酪乳或一碗汤”,并邀请他人共享这一仪式。重复的动作成为冥想,平凡变得非凡。
这一方法在1967年与作曲家James Tenney合作的计算机生成诗《The House of Dust》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延伸。Knowles建立了描述房屋材料、地点、光源和居民的四个词表。Tenney将这些列表转化为FORTRAN语言,IBM计算机通过随机组合生成了成千上万的四行诗。这件数字诗歌的先驱作品展现了Knowles的雄心:探索新媒体,同时保持深刻的协作性和人文维度。
Knowles的乐谱遵循一种节约手段的原则,让人联想到俳句传统,但又不仅限于此。它们与日本形式共享对当下时刻的极致关注,以及从日常中提取独特的能力。1963年创作的《Shoes of Your Choice》仅要求参与者描述他们所穿的鞋子。这一极简指令开启了叙事空间,展开个人故事、回忆和情感。鞋成为存在的转喻,成为展现言语的媒介。2011年,Knowles在白宫前向总统Barack Obama和第一夫人Michelle Obama表演此作品,证明形式简洁并不排斥机构认可。
声音维度在Knowles的诗歌作品中占据核心地位。她喜爱的反复出现的豆子图案因其”经济实惠且随处可得”的特性,成为乐器。1971年呈现的《Bean Garden》是一块大型扩音平台,覆盖干豆,访客踩踏其上,借此行动产生随机音乐。这种对声音作为诗歌材料的关注,使她与Fluxus运动的同时代人区分开来,后者往往将音乐作为他们反叛行为的主要目标。而Knowles并不寻求摧毁音乐,而是拓宽其边界,让普通物品潜在的音乐性得以呈现。
建筑作为可居住的书籍
诗歌构建了Knowles对语言与动作的处理方式,而建筑则为她关于空间与身体的思考提供了概念框架。她的”书本物件”颠覆了容器与内容、载体与文本之间的传统等级。1967年创作的《The Big Book》高达2.4米,由八页可移动页面组成,固定在金属书脊上。每页装有滚轮,能被物理翻转,为读者创造不同的空间与路径。作品中包含一座画廊、一座图书馆、一条草地隧道、一扇窗户,以及采集的家用物品:厕所、炉具、电话。书籍成为建筑,建筑成为叙事。
这件宏伟的作品在欧洲巡展,逐渐恶化,最终在圣地亚哥完全解体。作品的物质脆弱性参与其意义:The Big Book 并非设计为永恒保存,而是为了被体验、被操作、被穿越它的身体们磨损。这种反纪念碑式的艺术建筑理念,直接反对现代主义雕塑的传统及其对永恒性的追求。Knowles 更倾向于短暂而非长久,过程而非结果。
The House of Dust 延续这一思考,将同名计算机诗赋予建筑形态。1970年,Knowles 在加州艺术学院校园内建造了一座玻璃纤维结构,基于四行诗”一个尘土之屋 / 露天 / 阳光照射 / 由朋友和敌人共享居住”。这座建筑-雕塑承接课程、电影放映、野餐以及交换礼物。它作为一个活跃的社交空间而存在,而非一件供人凝视的作品。最初版本于1968年安置在切尔西一栋廉租公寓旁,被人为纵火毁坏,提醒人们那些冒险进入文化机构保护区外的艺术提案的脆弱性。
Knowles 的建筑方法根植于对现代艺术与生活分离的隐性批判。她可居住的书籍提供了功能主义建筑的替代方案:它们不响应任何具体需求,也不追求可衡量的效率。它们创造情境,而非解决方案。The Boat Book,是最近基于 The Big Book 的变体,献给她的渔夫兄弟,包含渔网、贝壳、鱼竿、水壶等承载记忆的个人物件。建筑由此成为个人故事的载体,承担情感传递的媒介。
“自由页”(Loose Pages)系列始于1983年,与造纸师Coco Gordon合作,将这一探索推向极致。Knowles 为身体的每个部位创建页面:人体脊柱取代了传统书籍的装订。在其他页面雕塑中,参观者可以用身体某部分字面意义地进入页面。Mahogany Arm Rest (1989) 和 We Have no Bread (No Hai Pan) (1992) 邀请观众在四到五米的空间中进行身体投入。身体成为阅读工具,建筑成为体感文本。
这种触觉空间的建筑理念使 Knowles 与同时代艺术家区别开来。当1960-1970年代的观念建筑多侧重视觉与理论层面时,Knowles 强调触觉体验。她声明:”我不希望人们被动观看我的作品,而是让他们积极参与,通过触摸、品尝、聆听指令、制作或实际拿取某物” [3]。她对积极参与的强调预示了后世理论家所谓的关系美学,同时始终避免落入壮观或说教的陷阱。
Knowles 的书籍建筑同样质问我们对知识及其传递的态度。通过让书籍可行走,她暗示阅读并非被动接受,而是积极探索,是身心的旅程。这一空间隐喻式的阅读呼应当代接受理论,同时又是其具体体现。读者不再面对文本,而是身处其中,被文本包围、穿越。
一种分享的伦理
艾莉森·诺尔斯的作品勾勒出一种以慷慨与关注为基础的艺术实践轮廓。与浪漫主义孤独艺术家的神话背道而驰,她始终优先考虑合作:1969年与约翰·凯奇合作出版《Notations》一书,1967年与马塞尔·杜尚合作创作丝网印刷作品《Coeurs Volants》,以及几十年来与无数表演者合作。她的双胞胎女儿杰西卡和汉娜·希金斯从小就参与她的表演。这种合作的维度并未稀释作品,反而增强了作品,创造了一个关系和交流的网络,构成了作品的核心实质。
她作品中反复使用豆类食品体现了这一伦理观。诺尔斯选择这种食物不是为了它抽象的象征价值,而是基于其具体属性:无处不在、价格亲民,是普遍的生存来源。《Bean Rolls》(1963) 是她早期的书籍对象之一,由一罐装满干豆和微小文字卷轴的罐头盒组成。摇晃盒子时,豆子发出拨浪鼓般的声音。该物件同时作为书籍、乐器和雕塑发挥功能。这种媒介的融合体现了其丈夫迪克·希金斯提出的”中介”(intermedia)概念,而诺尔斯以特别优雅的方式诠释了这一点。
看似朴素的媒介, , 沙拉、三明治、豆类或手工纸, , 不能掩盖她思想的激进性。通过选择普通的材料和动作,诺尔斯并非追求贫穷美学,而是表明一种政治立场:艺术不属于精英,不需要珍贵材料,不应令人畏惧。她的乐谱可以由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表演。这种艺术实践的民主化反对主导当代艺术世界的商品化体系。
自1972年以来,诺尔斯在苏豪区的阁楼居住并创作,将该空间转变为生活与艺术融合的永久实验室。她的经纪人詹姆斯·富恩特斯指出:”她最有力的作品正是她最短暂的作品”[4],强调了这种实践抗拒归档和保存的悖论。如何展出被吃掉的沙拉、被吃完的三明治、消失的声音?这一问题困扰着试图将弗拉克苏斯运动纳入文化遗产的机构。2022年在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及太平洋电影档案馆举办的回顾展,是首次大规模专题展,反映了这种困境:如何展示其本质在于表演行为本身的作品?
艾莉森·诺尔斯于2025年10月29日在她纽约的公寓去世,留下了一部持续提出关于艺术本质、其功能及其观众的基本问题的作品。她在六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展现了非凡的一致性,提供了与夸张展示和商品化逻辑的替代方案。她提醒我们,艺术可以从最简单的动作中迸发,共享的沙拉或摇晃的豆子都能开启沉思和共融的空间。在这个充斥着图像和信息的时代,她邀请人们放慢脚步,去触摸、去聆听、去参与,这种呼唤显得尤为强烈。诺尔斯的遗产不在于售出的作品或声望卓著的展览,而在于启发无数艺术家在平凡中寻求诗意,融入日常生活,将每一个动作都视为可能的乐章。她的低调正是她最高的优雅,她对戏剧性的拒绝是她最大的勇气。请仔细听豆子的沙沙声:那是一个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共享重于占有、存在胜过永恒的世界之音乐。
- Ruud Janssen, “Interview with Alison Knowles”, Fluxus Heidelberg Center, 2006
- Ellen Pearlman, “Interviews With Alison Knowles, July-October 2001, New York City”, Brooklyn Rail, 2002年1-2月
- Jori Finkel, “When Making a Salad Felt Radical”, The New York Times, 2022年7月18日
- Alex Greenberger, “Her Ordinary Materials: Fluxus Artist Alison Knowles on Her Carnegie Museum Show”, ARTnews, 2016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