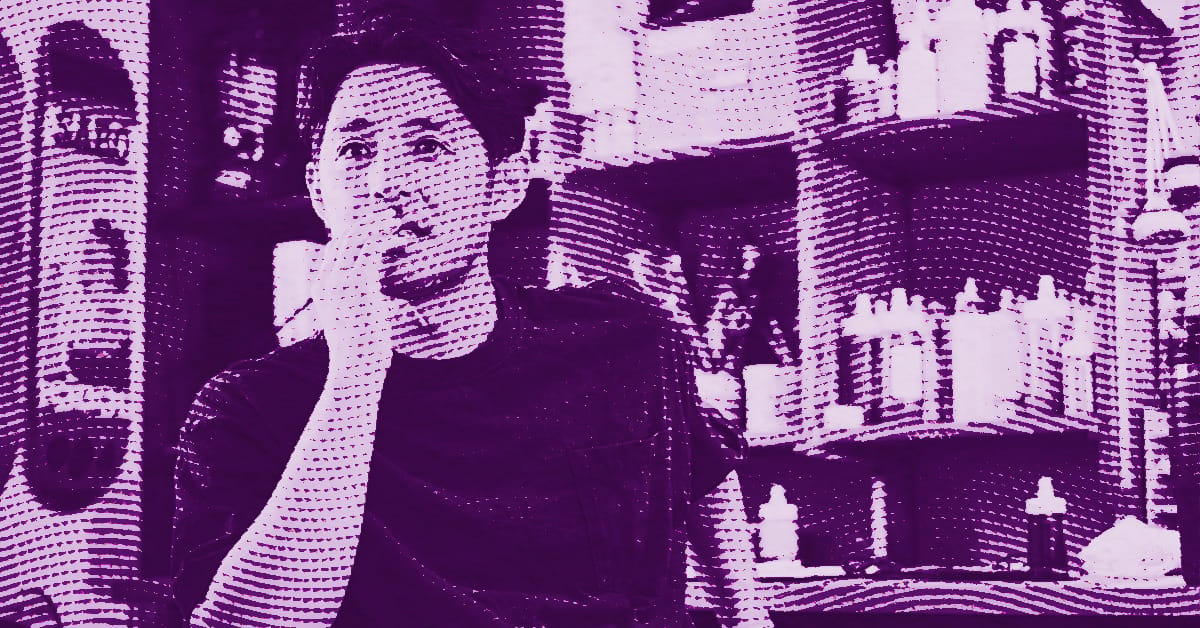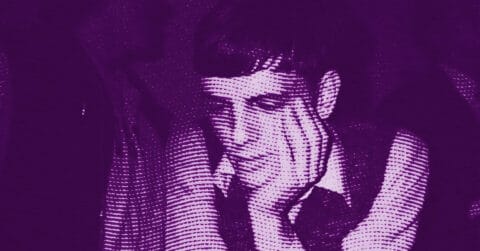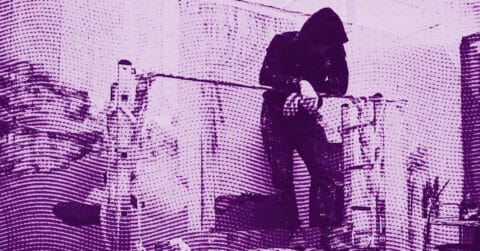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我要谈谈出生于1978年的日本艺术家花井佑介,他画出抑郁的人物,好像他是服用了迷幻药的新查尔斯·舒尔茨。你知道的,那些拥有怪异比例、充满忧郁的形象,假装拥有深刻存在感,蜂拥进我们的画廊?
让我们从他第一个执着开始:对60年代美国反文化的病态执迷。Hanai自诩为Rick Griffin的精神继承人,但他的作品不过是对一个他甚至未曾经历过的时代的苍白怀旧复制品。就好比萨特试图哲学化法国大革命,理论再多,体验的真实性却极其缺乏。他那些目光空洞的角色,应该体现Kerouac的垮掉派精神,实际上只是他从故乡日本幻想出来的反文化的肤浅漫画式夸张。
这种廉价的文化挪用让我想起那些由从未踏足日本的加州人经营的寿司店。区别是什么?至少食物并不假装正宗。这引出了他的第二个执念:通过他那些忧郁的角色对”普通人”的伪庆祝。
他那些蓄胡须、沮丧的人物设计,本应代表人类的脆弱性,实则不过是回收利用的视觉陈词滥调集合。这就像加缪决定将《局外人》画成漫画,却只用了长相像忧郁冲浪者的角色。瓦尔特·本雅明曾警示机械复制时代真实性的丧失,而Hanai更进一步:”机械地复制”了忧郁本身。
特别恼人的是,他每件作品都呈现同样的情感老调。他那些耷拉肩膀、目光迷离的角色已成为他的招牌,就像悲伤是一种可以批量销售的产品。罗兰·巴特本会对这个现代”酷失败者”的神话大加评论。这已成为一种和Warhol的Campbell’s汤罐同样可预测的品牌招牌,却缺乏后者那种使作品有趣的批评性讽刺。
别让我开始谈他和街头服饰品牌的合作。Theodor Adorno若见到忧郁成为一种时尚配件、售价250欧的连帽卫衣上的装饰图案,会在坟墓中翻身。反文化本该是一种抵抗形式,如今却沦为单纯的风格练习,一个为寻觅意义的千禧一代量身打造的Instagram友好美学。
技巧?毫无疑问,他确实具备。Hanai掌控线条,我承认这一点。但这就像一手漂亮字迹,却无任何有趣内容。他的构图有效,线条自信,但这一切服务于一个深度如马里布海滩上一滩水的世界观。米歇尔·福柯教我们寻找文化表征背后的权力结构。在Hanai那里,这些结构明显得令人尴尬: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对忧郁的物化,以及反文化的商业化。
他的展览更像是高端商品化的装置艺术,每件作品都经过精心设计,迎合那些将深度误认为是风格化抑郁的观众。这是艺术上的相当于青少年反复听Radiohead专辑后刚接触存在主义的体验,也许感人,但根本浅薄。
最令人沮丧的是花井确实有才华。我们可以从某些细节中看到,比如他捕捉身体紧张感的方式,有时他作品中的构图甚至达到了真正的感染力。但他似乎被自己创造的神话禁锢,成了被那个已成为”金色囚笼”的风格所束缚的囚徒。盖·德波曾警告我们:景观社会将一切变为商品,甚至忧郁,甚至反叛。
我忍不住想到让·博德里亚会怎样看待这一切。在这场仿冒的反文化中,悲伤成了Instagram滤镜,反叛成了T恤图案,花井成了我们时代的完美艺术家,不是因为他批判时代,而是因为他将其矛盾与浮浅完全体现了出来。
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目光低垂或望向远方,就好像在绝望地寻找一个他们无法把握的意义。这也许是他作品中唯一真实的东西:对一种难以捉摸的深度的不断追寻。但花井不断重复相同的姿势、相同的表情、相同的氛围,把这种存在的追寻变成了一套营销公式,跟他喜欢画的波浪一样可预测。
问题不在于花井是个坏艺术家,他不是。问题是他已经成了他所崇敬的反文化所反抗的那一切的缩影:一个量产内容的生产者,一个预包装忧郁、随时可穿的反叛制造商。如果他所敬仰的垮掉的一代能看到他们的遗产如何沦为奢侈品,他们或许会哭泣,不是因为花井喜欢表现的那种优雅的悲伤,而是因为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斗争被拿来收割的真正绝望。
当我们在空调画廊中品着香槟、用水晶杯杯盏敬酒时,我们都参与了这场盛大的骗局。我们为忧郁变成消费品、反文化变成时尚配件鼓掌。这或许就是花井艺术中真正的悲哀:不是他描绘的悲伤,而是他无意中表现的那个时代的悲剧, , 一个连反叛都成为注册商标的时代。
皮埃尔·布迪厄或许会认为花井的成功是文化资本社会区隔的完美体现。他的作品成了某些资产阶级阶层的地位象征,他们既想表现出既有文化底蕴又反叛、既敏感又酷炫。这就像是一辆豪华混合动力车,既能显示社会意识,同时又舒适地坐拥特权。
你知道这之间最讽刺的是什么吗?当我们在特权圈子里争论他的艺术深浅时,他的图像却在社交媒体上被无止境复制,变成表情包、手机壁纸、头像,甚至成了可怜的NFT。正如本杰明所言的机械复制,已变成数字复制,光环的丧失反而换来粉丝的增长。他那些悲伤的人物成了把忧郁误认为黑白滤镜的一代人的存在表情符号。
我有时想花井是否意识到这一切,他是否暗中嘲笑他的艺术正变成他所谓批判的东西。或者他也真诚,只是同样被他所支撑却又想揭露的系统所困。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的:艺术自我循环,陷入无限的自我指涉的怪圈。
那么,是的,去参观她的展览,购买她的印刷品,穿她的T恤。但别跟我说这是什么颠覆性的艺术,是深刻的社会批判。这只是高级情感设计,是存在主义营销,是限量版的反叛。也许这正是我们应得的:一种完美反映我们时代的艺术,不在于它所揭露的,而在于它已经变成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