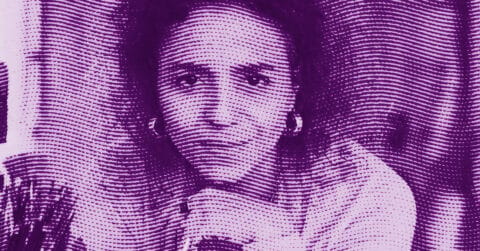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你们在当代艺术博览会上炫耀你们的深奥理论和知识分子的姿态。我将谈论1962年出生于台北的东珊卉,她是一位坚决拒绝屈从于你们那个自恋又自满的小艺术世界的艺术家。
在充斥着喧嚣装置和空洞概念作品的当代艺术景观中,东珊卉如一股平静却革命性的力量出现。她通过融合西方印象派和道家哲学,塑造了她的艺术身份,创造出超越文化边界和当下艺术市场痴迷的短暂潮流的作品。
她的”庭院”系列不仅仅是一组花园画作。这是对我们这个被速度和永恒变化迷惑时代的视觉宣言。在这些作品中,她捕捉了台北那些正被城市现代化无情吞噬的传统内院的本质。这些空间,拥有数百年的古树和覆盖青苔的石头,在她的笔下成为沉默的见证者,见证着正逐渐消失的千年智慧。每一幅画都是对沃尔特·本雅明所称的”光环”的深刻冥想,那是一种独特的远方显现,无论多么接近。那些庭院不仅仅是怀旧的遗迹,而是对我们城市环境中快速同质化的文化抵抗空间。
董女士在这些作品中对光的处理方式尤为耐人寻味。她不同于印象派画家们追求捕捉转瞬即逝的瞬间,而是创造出一种似乎从物体本身散发出来的光亮。就好像她实现了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眼与精神》中所描述的”第二道光”,这光不是来自外部,而是由事物本身发出的。这种独特的手法将她的画作转化为对感知本质的真正冥想。
在她的系列作品《黑色桌子的静物》中,她进一步深化了对空间与时间的思考。这些静物超越了传统的范畴,成为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显现”。画中反复出现的黑桌不仅仅是物体的承载,它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舞台,每一个物体、每一朵花、每一道影子都蕴藏着深刻的存在负荷。桌面深邃的黑色起到了西奥多·阿多诺称之为”不可显现的显现”的作用,营造了一种思索空间,邀请观者不仅审视画中的物体,也反思他自身与物质世界的关系。
她在作品中对空间的布局挑战了所有既有的规范。她既不遵循西方透视法则,也不遵循传统中国绘画的惯例。相反,她创造了加斯顿·巴什拉所称的”空间诗学”,其中空间关系不是由几何规则决定,而是一种更接近诗意而非透视的内在逻辑。这种方法在诸如《院中金色时光》(2023)之类作品中尤为明显,空间成为意识本身的隐喻。
她对色彩的运用同样具有革命性。在印象派试图捕捉自然光的振动时,董女士将色彩作为哲学工具。她那些深邃的绿色和丝绒般的黑色不仅仅是模拟自然,而是创造了吉尔·德勒兹称之为的”感受块”。每一种色调都载有冥想的意图,使观看过程转换为近乎精神体验,但又绝不陷入浅层神秘主义的陷阱。
她作品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董女士能够将平凡转化为崇高,且从不依赖当代艺术中极为常见的壮观手法。在《老庭院-快乐花圃I-II》(2021)中,她将一块简单的花圃提升至宇宙冥想的高度。这种把非凡显现于日常的能力,令人想起乔治·佩雷克在《非平凡》中所述的需求, , 质疑那些看似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已遗忘其起源之事物。
她对近期作品中植物造型的处理,彰显出对米歇尔·福柯所称”事物秩序”的深刻理解。画作中的植物不仅是简单的装饰元素,而是活生生的存在,参与了哲学家弗朗索瓦·朱里安所说的”无形大图”。这种方法在《院中梅花I-II》(2023)等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花朵成为无声宇宙戏剧中的独立角色。
她对传统的处理方式同样具有革命性。她既不像许多当代艺术家那样全盘否定绘画遗产,也不盲目屈从于传统主义者,而是与这一遗产进行批判性的对话。她对庄子哲学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于1993年撰写了一本相关著作,这使她能够超越传统与创新之间无意义的二分法。她由此创造了一种皮埃尔·布迪厄所称的独特”艺术习性”,既非完全东方,也非彻底西方。
在她近期的作品中,尤其是她的双联画系列,她更进一步推动了传统的融合。双面板的结构,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卷轴,在她的画笔下成为一个复杂的概念装置,质问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这种方法让人联想到雅克·德里达提出的”差异”理念,即存在与缺席之间的富有张力的生产性矛盾,从而产生意义。
使她的作品在当今尤为重要的是,她抵抗了当代艺术世界无节制的商品化。她的作品并非为Instagram自拍或壮观的拍卖设计,而是需要一种与我们持续分心文化相悖的关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艺术成为盖·德波所谓的反景象,是对景象社会的无声但有效的抵抗形式。
她作品中带有的女权主义维度,虽然从未被明确宣示,却深深根植于她的实践中。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强调的,在一个依然以男性主导的艺术世界中以女性身份进行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但董女士走得更远。她成功超越了性别刻板印象,同时创作出完全体现其女性敏感性的艺术。
她对静物的处理在这方面尤为具有启示性。传统上,静物被视为较为”女性化”的次要体裁,而她将其升华为深刻哲学思考的载体。在作品如《祥和的一天-粉红山茶花》(2023)中,她将简单的花卉布置转化为对存在本质的冥想,呼应了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所说的”女性的时间”,一种与父权线性时间相对的循环时间观。
她对近期作品中抽象的处理同样值得关注。与倾向于彻底与现实断裂的西方抽象不同,她的抽象是从对自然世界细致观察中有机产生的。这种方法让人联想到弗朗索瓦·于利安所描述的中国思想中的”无形大象”,其中抽象并非具体的对立面,而是具体的自然延伸。
她在构图中对负空间的运用尤为老练。画面中的空白不仅是简单的缺席,而是构成整体结构的积极存在。这种方法让人联想到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所称的”虚无之所”,这一概念超越了西方存有与非存有的对立。
她在”庭院”系列作品中对记忆问题的处理方式深刻感人,却从不落入煽情。那些在现代化推土机下消失的花园,在她的笔下成为皮埃尔·诺拉所称的”记忆场所”,是集体记忆凝结并寄托的空间。但与许多仅仅满足于记录消失的艺术家不同,董女士创作了将这一失落转化为美与思考源泉的作品。
董淑慧提醒我们,真正的创新不是拒绝过去,而是将其创造性地融入当代视野。她的作品证明了可以创作出根植于传统又极具当代性的艺术。她向我们展示,艺术的真正革命不在于戏剧性地摈弃既有形式,而在于对其细致而深刻的转化。她的作品活生生地证明,在一个被表演和瞬间统治的世界里,艺术依然可以成为抵抗与思考的空间。她提醒我们,艺术的真正激进性不在于表面的挑衅,而在于创造能够改变我们看待和思考世界方式的作品。
所以,是的,你们可以继续对那些华而不实的视频装置和空洞的表演惊叹不已。可是与此同时,董淑慧依然在创作那些即使潮流消逝多年后依然有意义的艺术作品。她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不需要喧嚣才能被听见,它可以轻声细语,却深刻触及人类灵魂。她的作品依然是默默而有力的抵抗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