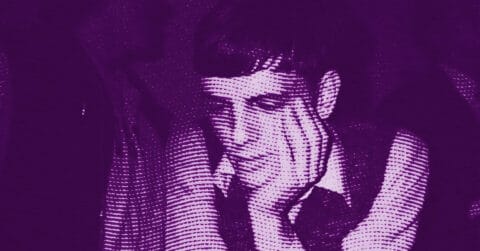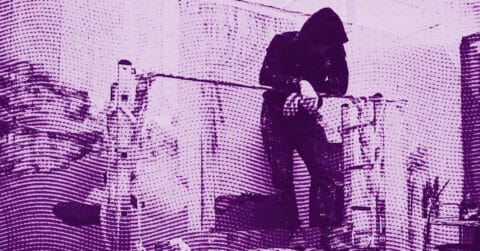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现在是谈论让-查尔斯·布莱斯的时候了。他1956年生于南特,是一位艺术家,能够把城市垃圾变成黄金, , 并不是那些炒家眼中的闪亮黄金,而是真正令人不安并持久的艺术之金。四十年来,他不断以撕下的海报作画,戏谑艺术体制。
1980年代,当大多数艺术家沉迷于一种如同卡拉OK之夜般无拘无束的自由具象时,布莱斯开辟了一条更深刻、更激进的道路。他最初绘制的巨大人物,肿胀的身体,微小或缺失的头部,仿佛肩负着世界的重担。这些怪诞人物、不成形的存在如同给善良艺术的脸上重重一巴掌。正如沃尔特·本杰明在其对艺术机械复制的思考中所指出的,这是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锐利回应。这些受困于画面空间、如同盒中沙丁鱼般的怪异形象,比任何哲学著作更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看看他1983年的《羞耻》,这幅高278×宽192厘米的巨幅双联画。两个巨人四肢夸张,似乎想逃离他们的框架,如同囚徒想摆脱牢房。他们笨拙的动作和怪异的姿势,比萨特所有存在主义的分析更能展示我们的存在焦虑。这是荒诞派戏剧的绘画版,是二维的贝克特。别告诉我这”只是”撕下的海报画作。这就像说《格尔尼卡》”只是”布面油画一样荒谬。
布莱斯的这段早期时期是对善良当代艺术的一记响亮耳光。他那些拥有巨大身体和小人头颅的角色,完美比喻了我们的社会:填满消费的身体,却被单一思维缩小了的头脑。正如西奥多·阿多诺所称的”否定辩证法”,这是一种拒绝与它所批判现实和解的艺术。
但别被误导,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形式练习或无端的挑衅。通过使用撕下的海报作为载体,布莱斯完成了一场激进的艺术转向。正如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所写,广告图像承诺一个转变为消费品的未来。布莱斯在这些被撕裂的承诺上作画,将商业的谎言转化为艺术的真理。载体上的意外、其鼓胀、撕裂,成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脸上的伤疤讲述着故事。
这种载体的选择绝非偶然。在一个被广告图像饱和的社会中,使用这些相同的图像作为原材料,既是政治姿态,也是美学行为。正如盖·德波会分析的那样,这是一种将”景观”反转回自身的方式。每一张被撕下的海报、每一层被撕裂的纸张,在他手中都变成了反消费社会的宣言。
自1990年起,艺术家为我们呈现了同样震撼的第二幕。告别了怪诞的人物,迎来了幽灵般的轮廓、在纸上跳舞的影子,如同柏拉图洞穴中的囚徒。巴黎国民议会地铁站成为他的现实版游乐场。一幅巨大的壁画,他的幽灵般的人物似乎在对我们匆匆而过者说:”看啊,你们这些匆忙的路人,这就是速度时代人类的变迁。”
这种演变不是断裂,而是一种必要的蜕变。庞大的身体变得纤细,直到成为虚无的轮廓,仿佛绘画的物质性已溶解于时代气息中。正如莫里斯·梅洛-庞蒂所说,这是”可见肉身”,即形式变得如此纯粹,以至触及无形之处。
琳达·诺克林会欣赏布莱斯如何系统性解构表现的法则。他那些无脸的人物挑战了我们的认同需求,挑战了我们对叙事性的期待。这是一种拒绝被简化为单一故事的艺术,像一个叛逆的青少年抗拒父母的命令。每件作品向观者发出挑战:”那么,你真的认为你能这么容易地理解我吗?”
因此,1990年代见证了布莱斯对新领域的探索。他冒险进入第三维度,创作”弹性失重”状态的半身像和头部雕塑。他与时装设计师合作,将轮廓转化为时装版型,玩味着身体作为社会构建的理念。这些实验并非偏离,而是他对人体形象及其变形研究的自然延伸。
在1998年的”量身定制”系列中,他将探索进一步推进,委托缝纫工作室制作他的织物作品。这一举动定会让马塞尔·杜尚会心一笑,他那位喜欢模糊艺术与手工艺界限的大师。这些纺织品作品宛如他绘画作品的幽灵,是他绘制轮廓的物质回声。
自2000年代以来,布莱斯以同样的破坏性大胆投身数字艺术。有些人会说他背叛了自己的绘画起源。但我认为他以惊人的连贯性继续他的探索。他的数字投影之于像素,如同他撕裂海报之于纸张:一种待转化、待超越的原材料。正如罗莎琳德·克劳斯所指出的,他在探索媒介本身的可能条件。
2013年,慕尼黑现代美术馆举办了”Die digitale Linie”展览,汇集了其数字作品。展览中可以看到流动的形态、跳舞的影子、如同电子梦境中形成又消散的人物。布莱斯在这里将对人物的探索推向了极致的非物质化。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会将此视为其媒介理论的完美体现: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我们与图像和身体的关系。
但我最喜欢布莱斯的地方是,他始终保持着抽象与具象、存在与缺失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近期绘制在广告海报正面的轮廓,就如同徘徊在我们消费社会废墟中的幽灵。这些人物从被抹去的口号间隙中浮现,创造出一种可以称之为”间隙政治”的艺术。与1980年代他翻转广告海报不同,他现在在印刷面上作画,让商业文本和图像的片段透过他黑色的人物轮廓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表明我们都被这些图像、口号以及商业幸福承诺所居住的方式。但这也是一种超越它们、将其转化为其他事物的方式。
在他自1980年代起工作于圣保罗旺斯的工作室里,离我曾担任客座策展人的梅格特基金会不远,布莱斯继续探索他为自己创设的独特领域。在这座改造为工作室的旧教堂厚墙之间,他以不减的热情继续他的追求。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一位没有想法、没有画作主题、也没有项目的艺术家。我的绘画是无意图的……”这种虚假的谦逊掩盖了深刻的真理:真正的艺术往往源自对所发生之事的完全开放。
肤浅的评论者会说布莱斯在重复自己,围绕他的执念打转。但这根本不了解他方法的本质。正如吉尔·德勒兹所写,重复不是同一事物的复制,而是差异的生产。布莱斯的每一新作都是对他绘画语言的丰富,深化了他对人体及其变形的研究。
让-查尔斯·布莱斯的作品不是世界的窗口,而是指向我们这个匆忙、分心、痴迷于图像的社会的镜子。每个从这些海报层中浮现的人物,都是我们一次性文化的幸存者,是我们与图像和消费复杂关系的见证者。正如雅克·朗西埃所言,这是”感知的共享”,重新分配了可见与不可见、能言与不能言之间的关系。
布莱斯恰恰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一位拒绝轻松贴标签、持续探索、实验并令我们惊讶的艺术家。在一个由市场营销策略和媒体炒作主导的艺术世界里,他保持了难得的严谨与真实,令人敬佩。
他的作品被收藏于世界顶级公共馆藏中,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到巴黎蓬皮杜中心,再到伦敦泰特美术馆。但真正重要的是,经历了四十年的创作后,他依然能让我们反思、质问并感到不安。他的艺术不是用来装饰新贵客厅,亦非为了社交媒体内容生成。它提醒我们,艺术依然可以是一种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体验。
那么,是的,请去看看她的展览。面对这些无面容的形象,它们如此像我们。让这些残缺的身体、这些神秘的身影扰乱你,那些如同我们人类危机幽灵一般徘徊在墙上的身影。如果你听不懂,那也没关系。你总可以去欣赏最新流行的Instagram装置艺术。但三十年后,当人们还在谈论Blais的时候,你那些流行的艺术家早已被遗忘了,不要来哭诉。
毕竟,这就是让Jean-Charles Blais伟大的地方:创造了一种超越时尚却又深深植根于他那个时代的艺术。一种关于我们人类处境的艺术,却从不落入感伤或肤浅。一种,正如Roland Barthes所说,达到符号开始做梦的那个境界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