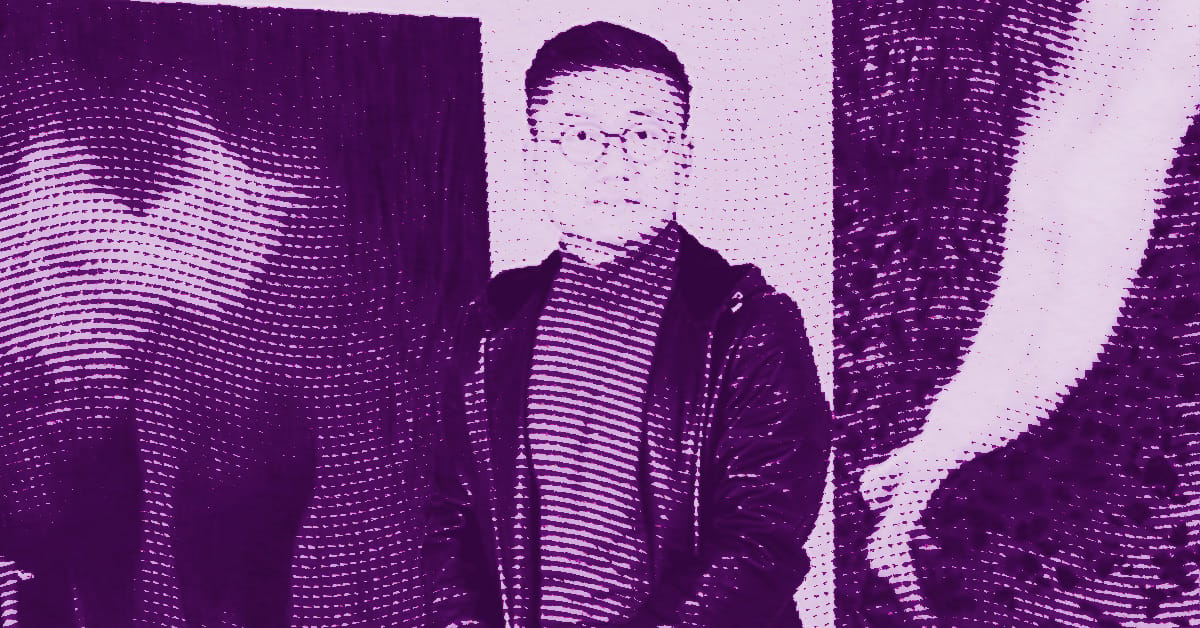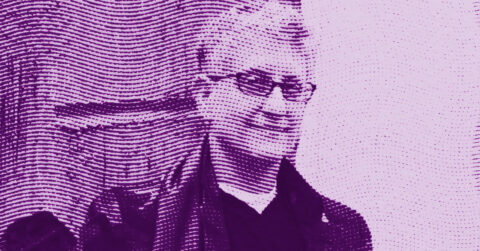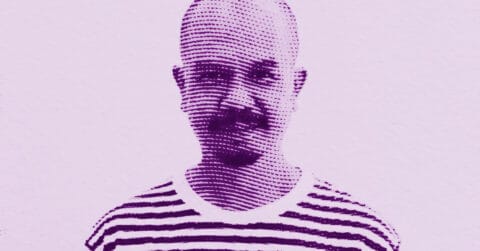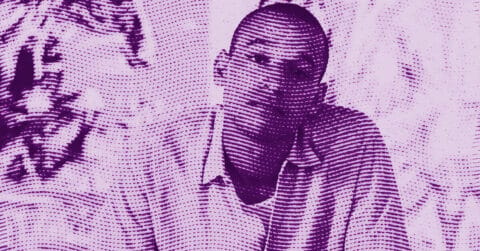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当你们为那些将画廊变成机场候机室的最新观念装置陶醉时,一位在巴黎生活了二十年的中国画家正耐心编织着一个以锐利视角质问存在的作品,这种视角应该让你们为自己的信念感到脸红。谢磊刚刚获得了2025年Marcel Duchamp奖,这一荣誉并非偶然:它表彰了他那种以极少有人敢于在当代艺术景观中宣称的严谨知识性,深入探讨人类模糊性的绘画实践。
谢磊1983年出生于淮南,曾在北京和巴黎美术学院学习,并在巴黎机构获得首个塑料艺术实践博士学位。他属于那种尽管受到观念艺术诱惑,却从未放弃绘画媒介的艺术家行列。他的博士论文题为”介于黄昏与黎明之间:当代画家的奇异诗学”,这一说法精彩地总结了他的艺术项目。正是在这不确定的时刻,白昼转为黑夜而界限模糊的瞬间,他的作品的全部力量得以寄托。
在2025年Marcel Duchamp奖评选中,谢磊展出了七幅巨大的萤光绿色画布,幽灵般的身体似乎漂浮在宇宙羊水之中。自由落体还是上升?画家拒绝定论,宁愿将其人物保持在他作品特有的形而上失重状态。人物轮廓刻意模糊、无明显特征,在似海洋深处又似夜林的植物背景中散发几近超自然的光芒。这种不确定性绝非形式懒惰,而是一种美学宣示:谢磊通过拒绝固定人物的身份、性别或完整人性,开辟了一个普遍的投射空间。
法国文学对他的想象力有着决定性影响。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是阿尔贝·加缪,其首部未完成小说《幸福死》[1](1971年)成为他2025年在Semiose举办的近期个展标题。这一加缪式矛盾修辞(如何既死又幸福?)深刻呼应谢磊的绘画路径。在这部1936至1938年间写成但由加缪本人弃笔的小说中,主角帕特里斯·梅尔索(Patrice Mersault)绝望地追寻幸福,甚至不惜犯下谋杀,以获取能让他充实生活的钱财。这一存在追求最终以对死亡的平静接受告终,与地中海自然融合,预示着《局外人》的主题。
谢磊占据了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这种张力,那一刻梅尔索(Mersault)病重且清醒,带着一种悲剧性的狂喜接受他的命运。他的画作正是在培养这种不确定性的区域:他所描绘的身体是垂死的人,还是处于神秘悬浮状态的存在?他们是在沉入深渊,还是在精神维度中重生?这种结构性的模糊符合加缪发展出的荒诞哲学传统,其中人类必须在一个缺乏内在意义的世界中为自己创造意义。谢磊的形象似乎体现了这样一个瞬间,即人类意识面临存在的无意义,但并未陷入虚无绝望。
“死而幸福”这个矛盾修辞在画家的色彩选择中找到了它的绘画对应。他那些水绿色、深蓝色、橙黄色环绕着他的人物,却并不对应任何自然肤色。谢磊调配他的色板时不使用黑色或白色,而是在蓝色和绿色之间叠加十层左右,获得那种恍若不真实、近乎迷幻的色调。最终效果创造了一种幽灵般的存在感:这些身体似乎既极端肉体又完全飘渺,仿佛物质正在光线中融化。这种色彩的二重性体现了加缪的直觉,即最强烈的幸福可以出现在接受存在有限性的瞬间。
当谢磊用单个词给他的画命名,如”Embrace”、”Breath”、”Possession”或”Rescue”时,他的做法类似于加缪为他的小说命名:以极致的意义浓缩,留下所有诠释的空间。一个吻可以是恋爱的拥抱,也可能是吸血鬼式的窒息。一个呼吸可以意味着生命的持续,也可能是最后一口气的逃离。这种词汇经济迫使观众面对自己对作品的投射,承认意义从未被赋予,而始终由观看者建构。在《死而幸福》中,梅尔索不是通过找到答案而获得幸福,而是通过接受存在人性的矛盾。谢磊的绘画提出类似的体验:它们不解决任何问题,而是提供一个沉思的空间,在此悖论得以共存。
在一次采访中,艺术家透露:”我的题材是奇美拉,是从我的记忆中提取元素的组合。看似平凡的场景总有非凡之事发生”[2]。这段表述表明他与加缪的世界观有着紧密联系,那里的日常生活瞬间转向荒诞,一名办公室职员可能在阿尔及利亚炽烈的阳光下变成凶手。谢磊的”奇美拉”是指现实破碎,揭示出另一种存在维度,既非完全活着,也非彻底死去,既非完全在场,也非完全缺席。‘死而幸福’正处于这中间状态:非最终状态,而是一个过渡,一个对立面相触的转折点。
谢磊与精神分析学,特别是朱莉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作品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他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他明确引用的理论参考中,有这位法国作家,她是保加利亚裔,其关于厌恶感、陌生感及身份极限状态的研究在谢磊的画作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克里斯特娃在《Étrangers à nous-mêmes》(1988)[3]中深入探讨了”陌生人”形象,不是被拒绝的他者,而是我们压抑的自我部分。她写道:”陌生人住在我们心中:他是我们身份的隐藏面,是破坏我们居所的空间。”这一观点,即最激进的他性存在于我们自身,深刻影响了谢磊的创作。
他的无脸、无明确性别、无清晰族群归属的形象,正体现了所有身份的构成性陌生。在拒绝赋予其人物可归类于某一社会、种族或性别类别的特征时,谢磊使他们处于”身份逃逸”状态。这些模糊轮廓的漂浮身体仿佛处于永久变形中,似身份永不固定而不断发展。克里斯特娃强调,认同内在的陌生人能使我们不去仇视外在的他者。谢磊的画作正遵循这一原则:通过描绘逃脱任何稳定分类的存在,令我们直面自身的根本不确定性。
克里斯特娃关于厌恶感的观念也在谢磊的作品中产生共鸣,尤其体现在他对身体溶解的处理上。根据克里斯特娃在《Pouvoirs de l’horreur》(1980)[4]中的定义,厌恶感指那扰乱身份、体系、秩序、不遵守界限、位置与规则的存在。谢磊笔下的人物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厌恶性:他们模糊生与死、物质与非物质、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他们的肌肤似乎溶入画面环境,轮廓融入光晕中,故意模糊主体与背景的界线。这种本体论的不稳定性在观众中引发一种富有成果的不安,观者难以在持续逃避的形态上稳定目光。
谢磊的绘画过程采用油画层层叠加,继而用刷子、纸张甚至手工刮擦,参与了这种溶解美学。有时画面中能隐约看到他的指纹,表明一种正逐渐消逝的实体存在。这种技法创造出复杂的触感表面,光线似乎从画布内部散发,而非反射其表面。身体成为独立的发光体,带有磷光,似乎拥有一种即使形态瓦解也依旧存在的生命能量。或许,这正是克里斯特娃关于忧郁症的思考与艺术家作品的共鸣所在。
在《Soleil noir : Dépression et mélancolie》(1987年)中,克里斯特娃探讨了主体经历一种无法通过语言符号化的失落的心理状态。忧郁症的特征是无法完成哀悼,对失去的对象有着矛盾的依恋,这个对象成为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谢磊的幽灵般形象可以被理解为这种忧郁状态的绘画化身:它们既不完全存在也不完全消失,如同无法离开生者世界的鬼魂般徘徊在画面空间中。它们幽灵般的光辉唤起了消逝之物的持久存在,强调了缺失的存在,这正是忧郁体验的定义。他近期系列作品中主导的水绿色,可以被解读为这种心理状态的流动性液态隐喻,没有清晰边界,主体仿佛迷失于致命的幻想之中。
克里斯特娃还发展了对心理母性维度的思考,探讨了先于任何身份认同建构的与母亲的原始联系。谢磊描绘的绿色和水域空间,以其包容性和沉浸感,必然让人联想到羊水,这一原初环境里胎儿尚未区分自身与外界。那些在画布上自由坠落或漂浮的身体似乎回归了这一前出生状态,试图找回失落的完整性。这种向最初无差异状态的倒退,是对逃避个体化痛苦、母子分离必然带来创伤的绝望尝试。
谢磊的创作明显受其夜间梦境的滋养,他在多次访谈中曾确认这一点。为马塞尔·杜尚奖项目,他从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出发:飞翔的梦境转变成坠落的噩梦。掌握弗洛伊德及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克里斯特娃极其重视梦境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梦境使人得以触及日间意识无法进入的心理区域,赋予焦虑和欲望以形态,梦境之外无法表达。谢磊的绘画如视觉梦境:遵循梦的逻辑,物理法则与身份法则被暂停,身体可以无重力漂浮,色彩不必再对应现实。这种梦境特质部分解释了他画作的催眠效果:它们将观者推入一种介于清醒与睡眠之间的第二状态,这正是谢磊本人创作时努力达到的境界。
这位艺术家描述了他的工作方法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思想和概念阶段,然后是身体和动作阶段。这种二元性让人联想到克里斯特娃对象征界与符号界的区分,即结构化语言的秩序与超越它的身体冲动的秩序。第一阶段对应象征界:选择图像,探索其多重含义,研究其文化共鸣;第二阶段属于符号界:艺术家让位于偶然性,”幸运的意外”,以及不受理性控制的动作自发性。这种掌控与放任的辩证法产生了智力与身体持续对话的作品,哲学思维体现在绘画材料中,却绝不沦为单纯的观念插图。
谢磊在其创作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可以这样表述:如何在绘画中表现模棱两可?如何以可见的形式呈现那些本质上拒绝任何固定或稳定界定的事物?克里斯特瓦指出真正的艺术中存在一种”反叛”特质,即其质疑既定秩序、扰乱令人安心的分类体系、揭示表面简单之下隐藏的复杂性的能力。谢磊的绘画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反叛性:它们抵制任何单一的解读,挫败观众对透明意义的渴望,强加一种难以拥有的美的迷惑体验。它们迫使我们接受存在无法消弭的不确定区域,所有矛盾无法皆被解决,某些问题必须保持开放状态。
这种对模糊性的接纳并非轻易的相对主义,而是一种伦理与审美的要求。在当今这个被清晰、高效和即时所困扰的世界里,每个现象都必须能在社交网络上几秒内被解释清楚,谢磊坚持担当复杂性。他的画作需要时间、耐心和稀缺的沉思准备。它们不会在第一眼就展露真容,而是缓慢展开,逐渐显露其意义层次。这种缓慢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对抗我们生活的全面加速、对抗无限”滚屏”的暴政,画家设定了一种冥想的节奏,使观众能够重新连接自我的内在世界。
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法布里斯·埃尔戈特(Fabrice Hergott)在谢磊的作品中赞扬了”对21世纪初本质的特别成熟表达”,在那个”缺乏参照物与眩晕已成为最常见感受”的时代。这种社会学解读不应使我们忘记这些绘画力量正体现在其拒绝当代轶事性质。谢磊并非像记者那样描绘我们的时代,而是捕捉其中深层的情感结构,即超越特定历史环境的存在焦虑。他那些幽灵般的人物既在谈论我们的当下,也在述说人类的普遍境况,这种形而上学的孤独是每代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面对的。
这是一位画家,他既没有放弃具象绘画,也没有放弃艺术的哲学抱负,他拒绝简单直接的表达,也拒绝完全抽象的表现,在一个不利于严苛创作的环境中,耐心地构筑了一部要求极高的作品。他获得马塞尔·杜尚奖的桂冠,不应被简单视为机构的认可,而应被看作一个集体需求的体现:那就是在面对谢磊的画作时,重拾当代艺术市场过于频繁地为了追求轰动和丑闻而忽视的深刻质问。这些悬浮于坠落与飞翔之间、存在与缺席之间、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身体,提醒我们:真正称得上艺术的东西不会解答任何问题,但会加深我们的疑问;它不会抚慰我们,却让我们更清醒地面对自身存在之谜。在一个充满瞬间影像和预制情感的世界里,谢磊为我们带来了变得珍贵的东西:那种聆听我们内心焦虑深渊低语所必需的寂静。或许,这正是所谓的幸福之死:接受直面令我们恐惧的事物,并在这一对峙中发现的不再是恐惧,而是一种奇异的宁静。这位画家不承诺幸福,但他向我们展示如何诗意地生活于自我矛盾中,如何将眩晕转化为绘画的素材,如何使构成我们不确定性的本质不成为弱点,而成为一种令人动容且必不可少的美的源泉。
- 阿尔贝·加缪,《幸福之死》,加利马尔出版社,阿尔贝·加缪文集,1971年
- 谢磊引言,发表于2025年马塞尔·杜尚奖展览目录,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
- 朱莉娅·克里斯特娃,《我们自己之外的人》,费亚尔出版社,1988年
- 朱莉娅·克里斯特娃,《恐怖的力量:关于厌恶的随笔》,缩影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