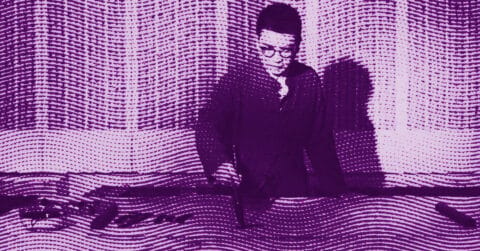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谭平并未循规蹈矩地无限重复相同的创作套路。这位1960年生于承德的艺术家,近四十年里系统地拆解了关于绘画应该或必须是什么的一切确定性。当大多数当代中国艺术家还在出口民俗与表面西化之间徘徊时,谭平开辟了一条独特道路,这是一种穿越文化边界而不自满的激进质疑。
谭平曾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后于1989年至1994年在柏林深造,他代表了那个经历中国当代变迁同时吸收西方艺术法则的关键世代。但与常有阵营之别的同时代人不同,他将东西方之间的这种持续张力作为其主要创作领域。他的作品不试图调和这些世界,反而探索那些产生新表达可能的摩擦区域。
解构的建筑
谭平的创作围绕一个自1990年代以来贯穿其所有作品的核心问题展开:”什么是绘画?”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隐藏着对传统绘画规范的系统解构。他的首批抽象作品源于1987年柏林工作室的一次意外:一块在酸液中浸泡过久的铜板,腐蚀了他刻画的人像,揭示了偶发性与纯质感的美。
这一启示促使他发展出后成为其标志的覆盖技法。与传统抽象艺术家构造作品不同,谭平采用减法和掩埋的方式。他的画布如埋藏的证据,每一层颜料覆盖前一层,营造出神秘的深度与多重时间感。艺术家称之为”无目的即是有目的”,强调无意识的行为[1]。
此方法类似中世纪建筑,那里大教堂经历数百年建造,融合各时代风格而不求均质。谭平的画作遵循类似历史累积原则,但方向相反:不是添加,而是覆盖;不是揭示,而是掩埋。每件作品因此成为时间性的纪念碑,层叠绘画史的缩影。
哥特式建筑教我们,美常源于对立力量之间的张力:推力与抗力、重量与升高、阴影与光明。谭平的作品遵循相同的辩证逻辑。他的大型画作,如《History》(2015年,300 x 400 厘米),呈现揭示与隐匿、存在与缺席、构建与毁灭的持续冲突。
这种建筑张力尤其体现在他自2016年以来创作的现场绘画中。这些作品突破画框,侵占展览空间的墙面,实质上改变了场地的建筑结构。画布上涌出的黑色颜料爬满画廊的白色表面,营造出一种空间对话,令人想起1960年代激进的建筑干预。而那些寻求惊人断裂的作品中,谭平更偏好渐进的渗透,温和却不可抗拒地侵蚀空间。
现代建筑学学会了与未完成的、片段的、被规划为废墟的元素共舞。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分解他的体块,安藤忠雄(Ando Tadao)雕刻空隙,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使形态流动。谭平,作为消失建筑师,建造那些注定被埋藏的绘画建筑。他的作品不像教堂般向光明升起,而是深入物质肥沃的黑暗,创造冥想空间,使观者必须学习新的地理观感。
“Overspread”系列(2013-2018)将这一逻辑推向极致。这些大幅画布,表面全黑,只有在长时间观察下才能显露它们的秘密。在表面的统一之下,隐约可见浮雕、纹理变化以及意想不到的深度。正如彼得·祖姆托尔(Peter Zumthor)的建筑在体验的持久中展现微妙之处,谭平的作品需要时间来驯服,给予视觉以细腻的培养。
这种埋藏建筑在理论上与马克·奥热(Marc Augé)关于现代”非场所”概念的著作相呼应。谭平是否创造了”非绘画”,即那些超越传统艺术类别的绘画空间?他的作品不具象,不讲述故事,不传达明确的信息。它们如纯粹体验的纪念碑般存在,是在作品与观众之间构建的感性建筑。
时间的书写与记忆的空间
如果说建筑揭示了谭平作品的空间维度,那么理解他的时间与记忆关系则应诉诸文学。他的作品确实通过叙事的累积进行,每一层颜料都添加一个不断重写的故事章节。这种方法立刻让人联想到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的写作,他通过记忆层层叠加构建小说。
在西蒙那里,过去不被叙述,而是与现在叠加,形成意识流中交织的时间性。他那绵延流动的长句,反复纠缠的修正,创造了一种类似谭平绘画叠加结构的建筑式散文。当西蒙写道:”我记得那天下雪,不对:下雨,不对:雪和雨同时下”,他文学上实践了谭平通过不断覆盖的绘画手法。
这位中国艺术家发展出的覆盖技法类似于这种持续修正的写作风格。每一层新涂的颜料都会改变、细化,有时甚至与之前的形成对立,但绝不完全覆盖。遗迹显现,隐约浮现,形成视觉幽灵,丰富作品解读。正如西蒙,毫无定论,一切皆可质疑、修正、覆盖。
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源自艺术家自2004年以来的研究,那一年他父亲患癌症,让他直面生命的脆弱。癌细胞,起初是恐惧的对象,后来成为了迷恋的焦点,成为一系列作品的灵感来源,在这些作品中,细胞的繁殖成为艺术创作的隐喻。这些”细胞”绘画不断增殖、转变,以一种既有机又破坏性的逻辑占据画布空间。
西蒙发展了一种类似的文学观念,将文学视为一种活的有机体,能够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异。他的晚期小说,尤其是《刺槐》(1989年),探索了写作的自我生成维度,文本似乎自行生长,遵循其内部逻辑,而非作者的意图。同样,谭平让他的绘画按照自身的动态发展,接受意外、修改和意外的转变。
这种开放作品的哲学在他的《Drawing》(2015年)系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艺术家探讨了绘画行为的最小界限。这些炭笔素描,每幅不到两分钟完成,捕捉了纯粹自发创作的瞬间。它们让人想起克洛德·西蒙的”瞬间摄影”,那些简短的文字捕捉了短暂的、转瞬即逝的真相。和这位法国作家一样,谭平明白,当代艺术必须学会捕捉瞬间,同时融入持久的时间维度。
他作品的时间维度在现场即兴绘画的表演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这些公共创作由视频记录,揭示了作为事件的创作过程。艺术家在观众面前作画,将私人创作行为转变为集体表演。这种戏剧化让人联想到新小说流派对文学与现场表演之间混合形式的探索。
记录这些表演的视频本身成为独立的作品。它们展现了艺术家的动作、创作节奏、以及贯穿创作行为的犹豫和决断。这些视觉资料类似于遗传批评中作家起草本,揭示了通常被隐藏的创作过程。
视频作品《CHI CHU》(2014-2015)将这一思考推向极致。这套炭笔素描系列,所有作品均在两分钟内完成,探讨了创作自发性的极限。标题本身唤起了中文的拟声词,暗示回归语言的原始根源。正如西蒙探索家族记忆的地质层,谭平深入考察创作行为的考古层面,寻回其最初的本质。
这种创作的考古学与当代对集体和个体记忆的关注相呼应。在数字技术改变我们对时间和历史的感知之际,谭平的作品提出了一种诗意的抵抗,其绘画以鲜明的物质性和缓慢的创作节奏,在即时性的世界中构成另类时间性的孤岛。
克洛德·西蒙曾写道:”过去只存在于它突然显现的当下。”谭平的作品体现了这种时间哲学:它们使自身创作的历史可见,将创作过程转化为艺术主题,把创作的时间视为作品的真正内容。因此,它们属于现代主义伟大传统的一部分,从普鲁斯特到西蒙,把时间作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核心对象。
消失的经济学
超越其审美维度,谭平的作品从根本上质问我们的时代及其经济和社会变迁。他的覆写作品提出了一种矛盾的经济学,其中价值源于破坏,积累通过减法完成。这种反直觉的逻辑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创生-毁灭循环的转变强烈共鸣。
当谭平有条不紊地用多层黑色油漆覆盖画布时,他实践了一种具有生产性的浪费形式,唤起了我们社会消费主义的过度。但与以生产销售再丢弃为逻辑的市场机制不同,他的作品将这种浪费转化为美,将破坏转化为创造。他的画作成为反生产力的纪念碑,成为经济效率让位于诗意无偿性的空间。
这种消逝的经济在当代中国背景中找到了合法性。谭平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国家的剧烈变革,这种对现代化的狂奔导致传统文化的大片消失。他的作品留下了这些变迁的痕迹:掩埋过去却不抹去,在似乎摧毁的行为中保护记忆。
“+40m”系列 (2012),这条雕刻在长达四十米木板上的单一线条,是这段思考的顶峰。这件展出于中国国家美术馆的作品提出了一种极简艺术经济学:一个动作,重复六小时,完成本质。在艺术过度生产的社会中,谭平找回了创造的原始手势,手工艺工作的迟缓古朴。
这种稀缺经济学与当代艺术膨胀形成鲜明对比。当艺术市场偏好不断创新和作品倍增时,谭平主张耐心与重复。他的作品不寻求取悦消费者的目光,而是需要时间、注意力和观众的个人投入。
他的现场绘画激进化了这一替代经济。这些短暂的作品注定在展览结束时消失,完全逃脱市场逻辑。它们无法被出售、收藏或资本化。它们存在于其展出纯粹的当下,提出了一种体验经济,而非占有经济。
这一短暂哲学呼应了关于我们生活方式可持续性的当代生态关注。面对环境危机,谭平的艺术提出了一种替代模式:更少物品,更丰富体验;更少生产,更专注转化;更少消费,更重视沉思。
他在2020年疫情期间创作的最新作品深化了这一思考。深圳Artron艺术中心的”2020”展览将建筑空间转变为整体作品,艺术家连续三天现场创作。这场马拉松式的表演提出了一种完全赠予的经济学,艺术家无偿奉献时间与精力。
谭平的作品同时质问我们与工作及生产力的关系。他长时间反复覆写的过程,反复绘画同一表面,既让人联想到佛教禅定,也让人想到工业工人的重复动作。这种两重性揭示了当代艺术工作的复杂性,既是创造的解放,也是生产的异化。
通过将破坏转化为创造,将浪费转化为美,将低效转化为诗意,谭平提出了对当代生产主义的实践批评。他的作品不只是揭露问题,而是体现了一种替代方案。它们展示了另一种时间、空间和物质的关系是可能的。在一个痴迷于优化和盈利的世界中,它们恢复了缓慢与无偿的尊严。
这种矛盾的经济在贯穿其全部工作的禅宗哲学中达到了顶峰。禅宗教导真正的财富源自简朴,圆满由空虚中显现,美从消隐中涌现。谭平的作品体现了这千年的智慧,同时在当代艺术背景下予以更新。他提出了一条通往艺术现代性的中国路径,既不模仿也不排斥西方,而是发明了自己的综合体[1]。
这种文化综合或许是谭平对全球当代艺术最珍贵的贡献。在全球化使艺术实践趋同的时代,他展示了真正的当代性可以从深入本土传统中诞生。他的作品既非单纯的中国式,也非西方式,而是在综合我们全球化时代多重遗产的能力上,坚定地属于当代。
从这个角度看,谭平发展的消逝经济不仅是艺术策略,更是一种文明提案。面对当代的生态与社会挑战,它提出了基于节制、沉思和尊重自然时间的替代道路。因此,谭平的艺术远远超越艺术界的边界,直接触及我们时代的根基。
永恒存在的艺术
谭平近作令人震撼的是它们创造了绝对存在的空间。他的大幅黑色画布、光影装置与现场表演营造出时间如暂停、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当下的环境。这种存在的品质或许是他对当代艺术最独特的贡献。
与那些寻求震撼或惊奇的作品相反,谭平的作品邀请观众进行长时间的沉思。它们只有通过耐心观察才会显露,逐步展现色彩和质地的细腻。这种对观者的缓慢要求在我们即刻满足与持续分心的时代,是一种抵抗的行为。
他的现场绘画将这种存在逻辑推向极致。这些超越传统画框、占据建筑空间的作品创造了彻底的环境,观众仿佛沉浸于艺术之中。作品与环境的界限模糊,形成了完整的感官体验,既启发身体也动员精神。
这对全面存在的追求根植于深刻滋养他工作的禅宗传统。艺术家深受中国传统禅文化和西方极简主义[2]影响。但谭平远非模仿传统形式,他创造了适应现代艺术条件与当代挑战的当代禅宗。
他近期的作品尤为探索艺术的这种冥想维度。”Internal Circulation”(2022)系列的画布展现出几乎单色的表面,最细微的变化都显得极为重要。这些作品需要受过训练的目光,能够在表面统一中感知到细微差异。它们教育眼睛去感受微妙,培养耐心的注意力。
这种细微美学与西方极简艺术的关注点相契合,但因其明确的精神层面而有所区别。当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或丹·弗拉文(Dan Flavin)追求形式纯净时,譚平旨在带来观众的内在转变。他的作品不仅是被凝视的对象,更是冥想的载体,意识转化的工具。
这种精神追求完全承认其政治维度。在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参照点在现代化压力下消逝,譚平的作品提供了精神滋养与稳定的空间。它们提出了一种另类的现代性,不基于速度和新奇,而是基于深度和持久性。
“2020”展览在深圳Artron中心完美展示了其艺术的政治维度。譚平在序言中写道:”在2020年,冠状病毒疫情的突然到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死亡的临近。在最黑暗的时刻,艺术成为了面对死亡时被紧迫的光明”[3]。这件现场创作的作品持续了三天,面对公众,将艺术行为转化为对当代焦虑的集体抵抗仪式。
其艺术的仪式性维度值得强调。他的长时间覆盖创作,公开表演,集体创作恢复了当代艺术中经常缺失的仪式感。它们提供了美学共融的时刻,艺术重新获得了其最初的人类学功能:将社区围绕共享的美与超越体验聚集起来。这种变革雄心在其国际多样的展览中得到特别呼应,从上海到拉脱维亚的罗斯科博物馆[4]。
譚平的艺术因此融入了对失去魔力的现代性精神抵抗的悠久传统。正如浪漫主义者面对初生工业化,历史先锋派面对资产阶级理性化一样,他提供了艺术恢复转化维度的另类体验空间。
这一雄心在他与其他艺术家和机构的合作中表现尤为明显。他与瑞士艺术家卢西亚诺·卡斯特利(Luciano Castelli)在2016年苏黎世Helmhaus博物馆的对话诞生了融合东西方艺术传统的混合作品。这些跨文化的相遇为真正当代的艺术展现了一条道路,能够综合我们全球化时代的多重遗产。
他近期工作的发展趋势趋向于愈加非物质化的形式,体现了对普遍性的追求。他的光装置、短暂的表演、视频创作超越了传统艺术类别,呈现纯粹的体验,带来美学恩典的时刻,在文化差异之外与所有人对话。
他艺术的这种普遍性维度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中国根源。相反,谭平展示了文化真实性可以成为通向普遍性的跳板,本土传统的深入能够催生出对全人类有共鸣的艺术提案。在这方面,他的作品为当代艺术开辟了一条宝贵的道路,当代艺术常常在身份闭塞与全球同质化之间摇摆不定。
这种传统与现代、本土与普遍、精神性与当代性的成功融合,使得谭平成为国际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表明另一种现代性是可能的,这种现代性不是建立在断裂和一张白纸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转变和创造性融合的基础上。它为能够调和人与失落传统,同时陪伴人们面对时代挑战的艺术开辟了未来之路。
面对我们时代所经历的多重危机:生态、社会和精神层面,谭平的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他的作品不声称能够解决这些危机,但它们提供了反思和恢复元气的空间,是赋予意义和希望的美与恩典的时刻。在这方面,它们完成了艺术最高的使命:向人类揭示其自身的伟大,并赋予其继续前行的力量。
- Artlyst,”Tan Ping: Art On The Edge Rothko Museum Latvia”,2024年6月9日
- 魏画廊,谭平传记,访问于2025年8月
- 谭平官网,传记1960,tanpingstudio.com(访问于2025年8月)
- 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对唱:谭平回顾展”,2019年6月15日至2019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