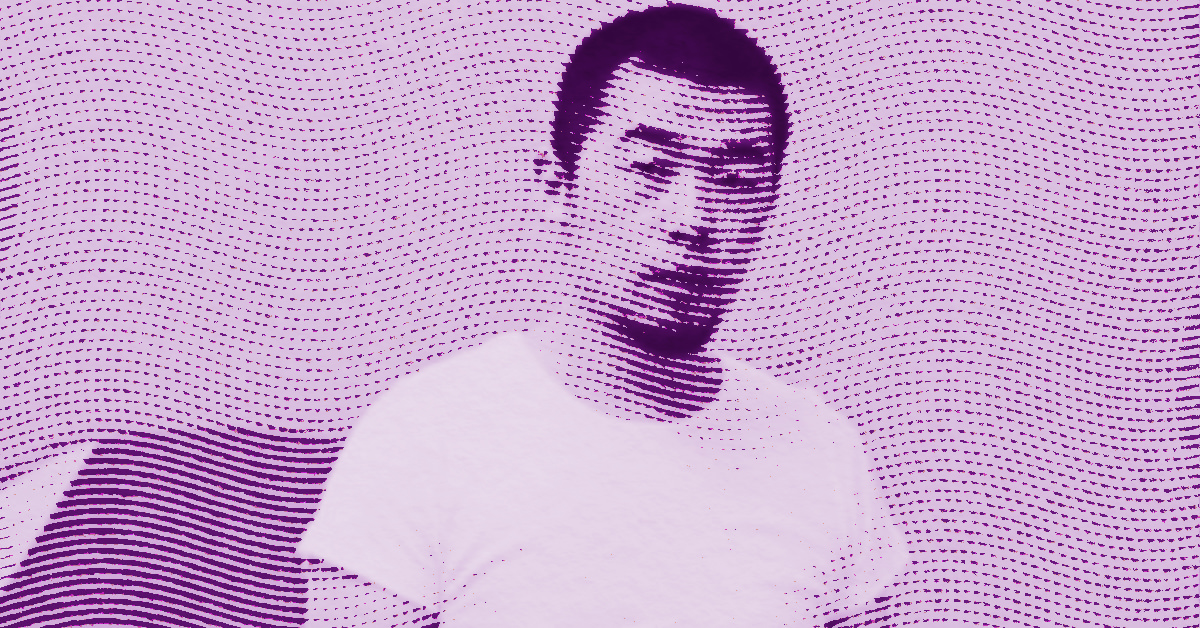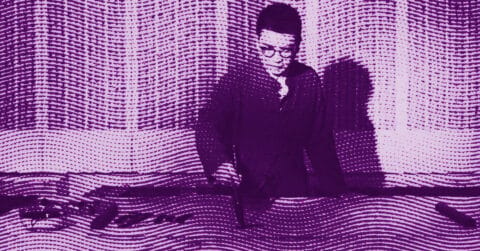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在当代中国艺术领域,趙趙作为他那一代最独特的创作者之一脱颖而出。1982年生于新疆,这位多面手艺术家在千年传统与激进创新之间游走,打造了一种既质疑又颠覆我们美学信念的视觉语言。
趙趙的作品跨越多种媒介,难以归类。绘画、雕塑、装置、行为艺术:他刻意拒绝风格禁锢,将这种多变性视为宣言。正如他2014年所言:”创作大量作品,正是为了不拥有固定风格”[1]。这一姿态体现了他的艺术观–形式必须服从表达的需求,每个项目拥有其自身的视觉语法。
现代性的波德莱尔审美
趙趙的作品与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思想有深刻对应。查尔斯·波德莱尔定义现代性为”转瞬即逝、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2]。这种辩证张力贯穿趙趙全体创作,尤其在其近期有关时间建构与记忆物件的系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他的装置作品如《控制》中,自然的葫芦在生长过程中被模具强制约束,艺术家将有机与人工的对立物质化。这些卡拉拉白大理石雕塑生动体现了波德莱尔美学观, , 现代美源于自然与构造的共存。该系列揭示了人类出于完美的目的干预如何不可逆转地改变生物形态的本质。
这位艺术家在《中华梯》中的装置作品中继续深化这一思考,该作品由传统竹梯复制成大理石制成的宏大装置。这些混合体化身为波德莱尔式的日常艺术变形:实用工具转为沉思雕塑,短暂的植物获得矿物般的永恒。趙趙从而实现了一种诗意的蜕变,将平凡升华为崇高,揭示最熟悉物品中隐藏的美。
这种方法还融入了重要的时间维度。正如波德莱尔捕捉到”转瞬即逝中的永恒”,趙趙凝固变革时刻以揭示其普遍意义。他的”粉色系列”绘画体现了这一实践:所画的桃花与鲜花在绽放与凋谢、生命与死亡间摇摆,在画面物质中凝结了生命的流光易逝本质。
鲍德莱尔现代性在赵赵那里找到了当代的翻译,融合了当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状况。这位艺术家捕捉了他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从中提炼出一种新的诗意,一种由传统遗产与城市现实碰撞中诞生的前所未有的美。将社会学观察转化为艺术创作的能力,构成了他作品中最显著的方面之一。
荣格集体原型的共鸣
赵赵的作品同样汲取了由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理论化的集体无意识深层结构。反复出现的普遍符号如梯子、山、蛋和动物,揭示了对支配人类想象的原型的敏锐意识。这些图案不仅仅是简单的图像符号,而是集体记忆的激活器。
装置作品”Météorites”完美体现了这一与荣格相关的维度。在将小行星碎片置于棉质匣盒中展出时,赵赵召唤出原始宇宙的原型,体现出人类对从天空降临物体的原始迷恋。这些来自外太空的石头成为了人类出现之前记忆的承载者,是超越我们理解的宇宙时间的见证。艺术家由此实现了荣格的”宇宙自我”原型, , 无意识中连接我们与普遍宇宙的那部分。
“Étoiles(星星)”系列延续了这一原型探索,将手势绘画与天文学参考元素相结合。画布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星团,既让人联想到星云,也隐约似细胞结构。视觉的这种双重性激活了荣格所说的”曼陀罗”原型,象征心理整体性,在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之间建立联系。
艺术家的多重自画像展现了他对荣格方法的另一面向。通过不同风格和表情的自我描绘,赵赵探索了”自我”的多重面貌,根据荣格,”自我”是整合意识与无意识的心理结构。每一幅自画像都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格面具”,揭示了当代个体复杂的身份认同。
这一原型维度因具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更加丰富,复杂了对荣格理论的分析。赵赵收藏并重现的”建盏”作为本地化的原型,承载着特定中国文化的集体记忆。这些千年古物激活了荣格所说的”罐”或”器皿”原型,象征接受性与精神转化,同时保持其独特的文化身份。
艺术家由此展示了集体无意识的普遍结构与历史和地理特征之间的结合。这种荣格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之间的合成,是他作品中最为复杂的维度之一,展现了一个能够同时思考本土与普遍的创作者。
创造性越界
超越这些理论关联,赵赵的艺术表现出自觉的挑战性。自早期艺术动作起,他就表现出打破既定规范的意图。这种批判立场非出于无谓挑衅,而是源于深刻的表现需求,是一种本能的欲望,用来质疑社会及艺术秩序。
他在公共空间的介入,比如从欧洲博物馆中采集作品碎片以创造新作品,体现了这种颠覆性的方式。这位艺术家不仅仅是批判艺术机构:他对其进行改造、重新占有,将其转变为创作材料。这种方法展现了艺术作为社会变革积极力量的理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审美评论。
“控制”系列延续了这种批判性思考,质询社会规范化机制。通过展示自然如何被人类干预而被限制和扭曲,趙趙隐喻性地与塑造个体的社会控制过程建立了平行关系。该作品作为当代标准化的隐喻,揭示了追求完美如何可能导致真诚性的破坏。
这层批判维度也体现在他与中国艺术传统的关系上。趙趙不仅没有拒绝这些传统,反而在当代语境中重新激活它们。他对建窑碗的研究就是这种方法的体现:艺术家不仅复制这些千年器物,更根据当代美学重新构想,揭示其隐藏的现代性。
地域依托
趙趙的作品与其原籍地新疆保持着深厚联系。这个历史上东西方交汇的边疆地区,使他的创作对文化认同和混合问题具有特殊敏感性。”塔克拉玛干计划”是这一点最成熟的体现:通过将沙漠的沙子带入展览空间,艺术家进行了地理上的转移,质疑归属与流放的概念。
这种地域维度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怀旧,也体现了对当代地缘政治议题的敏锐意识,特别是在”新丝绸之路”背景下最为显著。趙趙的作品质疑正在重塑中亚的经济与文化变革,揭示现代化与地方身份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
他最新展览中的”种子”作品反映了这一更新的地域关切。通过描绘菩提树种子,艺术家同时唤起佛教精神层面和植物学现实。这些作品作为文化萌芽的隐喻,暗示传统如何能在新环境中重生。
这种方法表现出一位意识到自己文化中介身份的艺术家。趙趙游走于北京和洛杉矶之间,代表了那批在多元世界中航行的中国艺术家,肩负着多重身份,这丰富了他们的创作。他的地域流动经历滋养了关于艺术形式普遍性以及其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思考。
因此,趙趙的地域扎根并非地方主义,而是一种利用本土特色以达到普遍性的艺术策略。这一做法植根于中国古老的艺术传统,该传统强调扎根是精神升华的条件。艺术家通过将这一理念适应当代全球化现实,对其进行了现代更新。
赵赵的艺术因此呈现出一个文化传承与当代创新之间的卓越融合。他能够结合西方的引用与中国传统、概念方法与手工技艺、批判立场与诗意感知,使他成为其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创作者之一。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他的作品为理解我们时代的转型提供了关键的视角。
他近期关于建窑碗的作品完美展示了这种综合方法。通过结合历史研究、当代创作和美学反思,这位艺术家展示了艺术创作如何更新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这种做法彰显了一位成熟的创作者,能够超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无效对立,打造真正当代的艺术语言。
- “赵赵:创作如此多作品,正是为了不拘泥于某种风格”, 天津艺术网, 2014
- 查尔斯·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