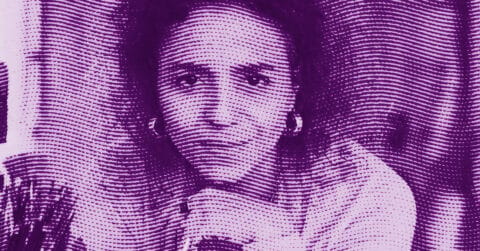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当我谈论一位颠覆我们对当代中国绘画固有认知的艺术家时。郝量,1983年生于成都,不仅仅是一个回收传统的画家,他以内在爆发的精致傲慢,使宋代大师们在坟墓中翻身。
这位丝绸画小天才,成长于电影世家,在收藏家、张大千弟子的教父熏陶下浸润艺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时间不再是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灌输的那条直线的世界观。郝量的时间是博尔赫斯式的迷宫,时代如同宇宙芭蕾般优雅碰撞。博尔赫斯本人会为这些作品鼓掌,这些作品宛如他最令人眩晕的小说,现实、过去与未来在一场死亡之舞中交织。
以他的杰作《The Virtuous Being》(2015年)为例,这是一幅超过9米长的横幅。这作品不仅仅是中国园林的漫步,它是一台时光旅行机,粉碎我们的时间坐标,如同钉锤击碎达利的钟表。明代王世贞的园林逐渐转变为现代游乐场,摩天轮如错乱的时钟旋转,将车厢投射穿越世纪。这是博尔赫斯与华特·迪士尼在一个道家哲学家的狂热梦境中的相遇。
但是郝良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杂耍者,他不是在玩弄对艺术史的俏皮暗示。他对丝绸绘画技巧的掌握,继承了国画的传统,如此精准,几乎达到手术级别。每一笔都是对时间织物的切割,每一个灰色的微妙变化都是中国文化记忆中的地质层。这就像沃尔特・本雅明将他的历史理论转世到了成都画家的手中。
系列作品《潇湘八景》(2016)完美体现了这种方法。这八幅宏伟的画作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绘画经典主题的简单再现,它们是对当代视觉关系的深刻冥想。郝良以哲学神经外科医生般的精准解剖了我们与影像的关系。在《潇湘八景,心灵之旅》中,他将传统地图转化为精神景观,其中空间如爱因斯坦的梦境般弯曲。就像马丁・海德格在阅读庄子后开始了风景画创作一样。
郝良的绘画技巧令人叹为观止。在丝绸这个细腻如细胞膜的材质上,他叠加了极其细微的墨水和矿物颜料层次,创造出令人眩晕的深度效果。他的灰色不只是黑白的简单混合,而是扩展中的宇宙,是色彩可能性的新星云,令人联想到哈勃望远镜拍摄的照片。每一幅画都是微缩的宇宙,是视觉弦理论,维度交织如科幻小说般复杂。
在《无尽山水》(2017)这件近10米长的作品中,郝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让明代绘画理论家董其昌与瓦西里・康定斯基对话,仿佛他们注定要相遇。康定斯基的抽象形体并非作为入侵者渗透进传统中国山水,而像长久失散后重逢的亲戚。这是一个概念上的绝妙打造,将艺术史变成一个量子游乐场,影响穿越所有时间方向流动。
艺术家不仅仅是在历史参考中玩杂耍,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视觉语言,超越了既定的类别。在他的肖像画中,面孔如同穿越数世纪冥想的幽灵,从丝绸中浮现。他的风景画并非现实地点的再现,而是精神的图谱,每座山都是凝结的思想,每条河流是意识流。
郝良处理时间性的方式是革命性的。传统中国艺术家追求在山水中捕捉永恒,而他关注的是当下瞬间复杂矛盾的全貌。就像亨利・柏格森给禅师上了绘画课。他的作品中的时间不是事件的线性连续,而是同时发生的体验星座,跨越时代相互呼应。
他的作品《神曲 II》(2022)在这方面尤为震撼。透过既象征现代监狱栏杆又如丝绸纤维的网格,我们看到一幕既可能发生在但丁的地狱也可能发生在现代城市公园。一个低头走路、裹着冬衣的人忽视了栖息在裸树上的恶魔。这是对我们当代状态的寓言, , 非凡与平凡彼此冷漠地共存。
这种将不同绘画传统交织在一起的能力不仅仅是一种风格练习,更是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回应。郝良并不试图调和古今,而是想表明这种分裂本身是一种幻觉。在他的作品中,传统不是一种负担,无论是承受还是拒绝,而是一种思考当下的活生生的工具。就好像瓦尔特·本雅明和马丁·海德格尔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约会,讨论数字复制时代的光环。
郝良最令人瞩目的,或许是他让看不见的东西变得可见。在《伤悲琴》(2023)中,他将诗人李商隐的忧郁转化为一系列风景画,忧伤似乎化作了形态。暗淡的色彩、虚无的形状、抽象与具象间微妙的过渡,创造出一种超越语言和文化屏障的视觉诗意。这是纯粹的联觉,绘画成为音乐,音乐化作情感。
高丽最近在嘉戈西亚画廊的展览表明,他不仅是技术大师,更是真正的画笔哲学家。他的作品不是透视世界的窗户,而是反照我们自身复杂时间性的镜子。在这个痴迷即时性的时代,他让我们明白,每一个当下都蕴含着过去的回声和未来的种子。
郝良的艺术是对中国绘画当代性问题的回应。它不仅仅是使传统现代化或使现代性传统化,而是创造一个新的绘画时空,在那里矛盾得以共存而不必解决。这是思考的艺术,呼吸的艺术,活在我们时代节奏中的艺术,同时脚踏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