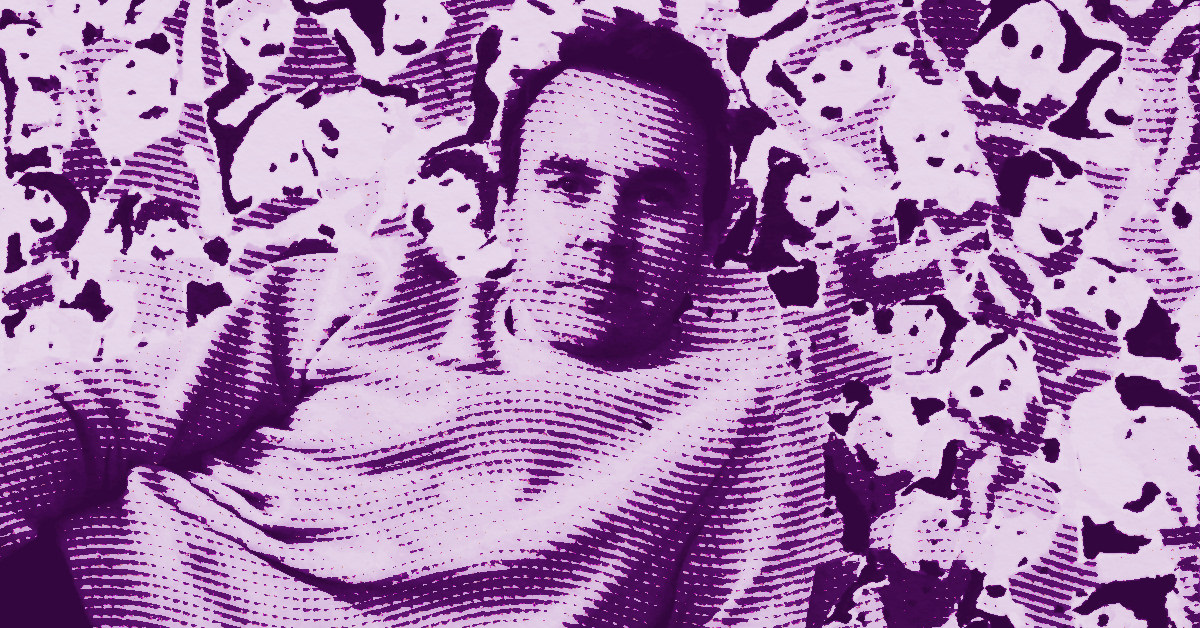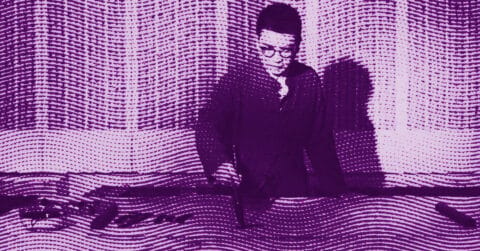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阿尔伯特·威廉既不是当代绘画的救世主,也不是其掘墓人,而是更有趣的存在:一个无畏的讲述者,将我们日常的小苦难转化为色彩斑斓的表演。这位比利时人,自学成才,以十二岁孩子的自发性和业余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作画。他的画布上充满简化面貌的人物,他们处于讽刺与荒诞并存的情境中:婚礼上宾客的争斗,葬礼上的疯狂舞蹈,永无止境的康加舞曲如同寓意我们人类处境的隐喻,在画布上蜿蜒。
威廉属于那一代理解当代艺术有时过于严肃的艺术家。他的丙烯画色彩鲜明大胆,故意摒弃任何技术上的完美追求。这种方法奇妙地呼应了亨利·柏格森关于笑的理论 [1]。这位法国哲学家解释喜剧源于”机械强加于生命之上的东西”,这似乎恰好用来描述威廉的世界。他那动作僵硬、表情凝固的人物,活跃于社会规范破碎的情境中。
柏格森的影响超越了单纯的机械笑点。威廉似乎直觉地把幽默作为社会揭示的工具。他那致敬布鲁盖尔的密集人群画作绝非中立。它们显现了我们的行为自动反应、群体本能以及人类即使在最非凡情况下也会表现出可预测行为的倾向。正如柏格森所言,”当一个人让我们产生一种东西的印象时,我们就会笑”,威廉则用画面诠释了此观察。他那些线条简洁的小人物变成了原型,”东西”,揭示我们自身的社会机制。
这一社会学维度在威廉笔下从不沉重,区别于许多用理论引爆观众的大师。这位比利时艺术家采用堆积和视觉饱和手法。他的构图细节丰富:警方车辆迷失于混乱中,广告牌不合时宜,次要人物在主场景边缘经历着自己的小戏剧。这种方法让人联想到乔治·西梅尔关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 [2]。这位德国社会学家把现代性描述为持续刺激的体验,个体需不断筛选大量信息以心理上应对都市生活的强度。
威廉将此分析转化为他的”城市混沌”. 他的作品诸如《拳击赛》和《葬礼》成为社会观察实验室。每个人物都过着自己的生活,漠视中心戏剧,营造出现代社会特有的视觉噪音。艺术家不做评判,只做观察;不做谴责,只做展示。这种友善的中立性使他的作品接近西梅尔的精神,后者拒绝对社会现象进行等级划分,偏爱在其复杂矛盾中进行分析。
威廉的原始技法远非缺点,而是一种连贯的审美选择。他那些肢体错位、面部简化的角色逃脱了现实主义的陷阱,更好地抓住了他们所经历情境的本质。这种图形简化使他的构图几乎本能地能够被立即解读。我们瞬间能理解发生了打斗、庆典变得失控、典礼陷入混乱,而无需破解每个主角的心理细微之处。
如此简约的表现手法显示出艺术上的聪慧。威廉明白,在这个图像过载的时代,需要简化的视觉代码来吸引注意力。他饱和的色彩和强烈的对比在当代文化的环境噪声中充当信号。艺术家并非试图与同行的技术复杂性竞争,而是创造了自己的视觉语言,完全承担了局外人的身份。
威廉的幽默从不无缘无故。他用幽默作为解读我们时代荒谬现象的框架。他的”拳击比赛”里,除了拳击手外人人争斗;他的”葬礼”变成了舞池,揭示了我们社会仪式的失调。艺术家实行一种视觉人类学,带着调侃的态度记录21世纪人的部落行为。
这种方法在我们这个被社交网络和高速连接标记的时代引发了特别共鸣。威廉实际上在Instagram上发现了他的初期收藏家,这个平台偏重于瞬时视觉冲击而非长时间凝视。他的作品在数字环境中运作完美:它们吸引眼球,引发微笑,易于分享。但与许多社交网络制品不同,它们能经得起深入检视。
威廉商业上的迅速成功既令人质疑又引人着迷。他的油画估价在11,000至17,000欧元之间,常常以估价十倍价格售出,2023年一幅叫作”The mountain air provided a pleasant atmosphere”(2020)的画作甚至达到了215,000欧元。这一现象揭示了对一种即刻可接近艺术的需求,它打破了主流概念艺术的晦涩难懂。收藏家,尤其是亚洲收藏家,似乎在威廉作品中找到了一剂对抗当代机构艺术庄重性的良方。
这种突然的人气不应掩盖威廉艺术项目的连贯性。艺术家多年发展出识别度极高的世界观,布满重复出现的人物和典型场景,逐步构成了个人神话。他的系列”Everything”包含一百幅描绘日常生活物品与场景的画作,展现了超越幽默轶事的整体抱负。
威廉自认是古老画家彼得·布鲁盖尔的传承者,借鉴并调整其宏观视角于当代现实。如同这位杰出前辈,他擅长合唱式构图,每个元素都为更大整体贡献。但布鲁盖尔微妙地持道德评判,而威廉则只是善意地观察。他的目光从不谴责,只是戏谑人类矛盾,却不试图解决。
这种旁观者的疏离姿态赋予他的作品意想不到的纪录片特质。一百年后,历史学家或许能从中发现宝贵的时代线索:我们的服饰代码、休闲方式、集体焦虑。威廉用现成手段拍下了时代气息,无意间创造了一份关于当下的视觉档案。
这位艺术家本人也声称他的作品具有见证意义。”我画的是21世纪,”他简单地宣称[3]。这种以记录为目的、没有理论夸张的野心,将他的作品纳入贯穿艺术史的写实传统。无论是夏尔丹、霍珀,还是印象派画家,许多艺术家选择见证他们的时代,而非美化它。
Willem故意采取快速的绘画技巧,服务于这种紧迫的记录需求。艺术家在最多四十八小时内完成一幅画,优先考虑自发性而非完美。这种快速的执行保持了观察的新鲜感,避免反思掩盖最初的观察。Willem绘画的方式就像其他人做笔记一样,固定住瞬间,免于其消逝。
这种工作方法也体现了对当代艺术工业的一种抵抗形式。拒绝技术上的完美主义,Willem逃避了主流审美标准。他既不寻求打动策展人,也不满足批评界的期望。这种独立性让他得以保持视觉的真实性,这在一个经常被市场逻辑塑造的领域中是一种稀有品质。
Willem的非典型经历,他在36岁时重新发现绘画,反映了当代艺术世界的变革。在一个学术课程标准化的时代,他自学成才的身份显得异常突出。艺术家逃避了教授们的影响,塑造了自己独特的美学,既汲取流行文化,也借鉴艺术史。
这种异端培训或许解释了他的风格的独特性。Willem毫无顾忌地混合了多种影响:构图上受布鲁盖尔影响,人物形象表现为洛瑞式风格,内索尔的狂欢精神也在其中。这种融合对一个受到正规培训的艺术家来说可能显得杂乱无章,但在他身上却产生了出人意料的连贯性。
Willem的崛起恰逢当代艺术中更广泛的叙事造型回归运动。在经历数十年概念主导之后,新一代艺术家开始重新发现表现的乐趣。 Willem融入这一潮流,但并不宣称承担修复的使命。他只是简单地画下自己所见,运用自己掌握的手法。
这种谦逊也许是他的主要力量所在。在一个常被自身理论束缚的艺术环境中,Willem呈现出直接可读、立刻打动人的艺术。他的画作在多个层面上起作用:对一些人来说是色彩斑斓的表演,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社会讽刺,对第三者来说是人类学见证。这种无意的多义性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投射自己的理解。
Willem体现了一种民主艺术观念,面向大众开放,但又不陷入浅薄。他的作品既能吸引艺术爱好者,也同样适合新手,无论是收藏家还是路人。这种在当代艺术中罕见的普遍性,或许是其公众和商业成功的原因之一。
这位比利时艺术家巧妙地结合了娱乐性与艺术要求。他的画作既娱乐大众又不流于迎合,既发人深省又不矫揉造作,既感人至深又不动情过度。达到这种恰如其分的平衡十分不易,彰显出他虽为新晋艺术家,却具备真正的艺术成熟度。
阿尔伯特·威廉提醒我们,艺术仍然可以在不放弃其批判维度的情况下令人惊喜、娱乐和感动。在一个经常可以预测的艺术景观中,他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对熟悉的现实有了新的视角。他的作品证明,从最简单的元素出发:画笔、颜料,以及对世界景观的敏锐目光,仍然可以发明一种原创的造型语言。
- 亨利·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的尝试,巴黎,费利克斯·阿尔坎,1900年。
- 乔治·西美尔,”大城市与精神生活”(1903年),载于现代性的哲学,巴黎,佩约,1989年。
- 阿尔伯特·威廉,引用自安妮·阿姆斯特朗,”认识阿尔伯特·威廉,这位自学成才的比利时画家,他的幽默画作突然在拍卖会上获得六位数的价格”,Artnet新闻,2022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