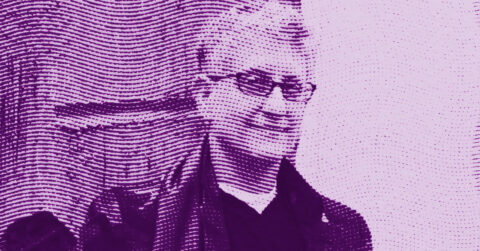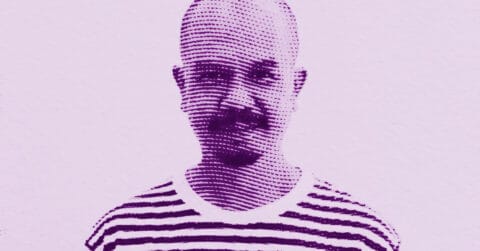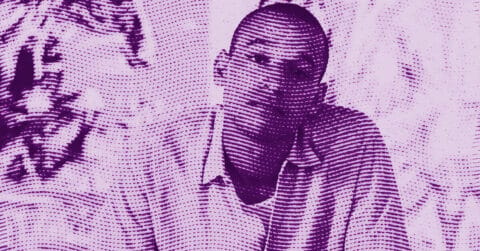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Bianca Bondi 绝非让你们无动于衷的人。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南非与意大利艺术家,十余年来构筑一个有生命的物质与无形间对话的世界,炭化衣柜与盐晶共存,记忆建筑与古文明遗迹交织。2024年米迪奇别墅驻地艺术家,2025年Marcel-Duchamp奖决赛入围者,Bondi 以其从容不迫的无畏实践,成为当代艺术不可忽视的存在。她不驯服自然,而是归还自然权利;不冻结时间,而是歌颂其必然流逝。
建筑作为缺席的舞台
Bondi 的作品首先是一场对栖居地的冥想,关于我们为自我保护建造的结构,最终被我们短暂痕迹所染。她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装置Silent House,生动体现了这一思考:一整间被居住者腾空却充盈其幽灵存在感的房子。这不仅是一处废弃的居家空间,而是一份失落亲密感的敏感地图,是离去后的地理拷贝。磨损的家具、脚盆浴缸、生锈的金属床框,共同构筑一种非悲悯的荒凉地理。这些物件反射着一种悖论的尊严,像沉默见证者,目睹躯体与灵魂的流转。
这位艺术家不仅仅是将家具摆放在展厅中。她编织真正的建筑戏剧,每一元素在缺席叙事中皆有精准角色。炭化衣柜垂直固定于墙,不再是单纯置物家具,而成为通往未知彼岸的门户,是拒绝熄灭的记忆烧成圣物。此垂直化动作将平行于居家生活的调度升华至宗教般的高度,暗示建筑不仅具功能,更具象征意义。Bondi 自言:”我总爱凝视祭坛,那些为超越我们自身,为诸神而设计的空间”[1]。此言点亮其创作全貌:每座装置皆为献给赋予材料神秘力量的世俗祭坛。
邦迪的建筑从不静止。它是一个过程,是变形与分解。她的装置中融入的盐水池宛如化学钟表,不通过指针的移动,而是通过盐在表面的缓慢结晶来标记时间的流逝。盐,这一在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材料,同时具备保存剂和腐蚀媒介的双重属性。它既保存又毁灭,正如人类记忆扭曲它所声称保护的事物。在《Silent House》中,盐逐渐覆盖物件一层白膜,仿佛房屋本身分泌出自己的殡葬物质,自己的矿物裹尸布。
对橱柜、展示柜、箱柜的细致关注揭示了她对亲密建筑空间的痴迷,这些储藏的微观空间集中反映了我们与物品的关系。邦迪收藏古董家具,尤其是那些我们已无法确定其内装究竟是香料还是药品、疗剂还是毒药的药柜。这种语义上的不确定令她着迷:它模糊了护理与危险、厨房与实验室、家务与科学之间的界限。橱柜因而成为回声室,回响着它们曾存放物件的各种可能故事。借用邦迪巧妙运用的一个概念,它们的光环并非源自形式之美,而是源自它们作为反复动作的无声见证者的能力,那些黑暗中寻找瓶罐的手。
邦迪眼中的房屋从不封闭自守。它溢出、扩展,渗透展览空间。装置创造出室内景观,使观众难以分辨自己进入的是房间、花园还是圣所。这种类型的混淆是故意的:旨在重现那种原始的居住体验,发生在建筑划分为独立房间与分离功能之前。当邦迪在地板上铺设三吨盐时,她并非仅制造视觉效果;她将地板转变为矿物海滩,成了家庭沙漠,脚步仿佛踏入一场化学雪。地面变得不稳定、令人不安,而这种物理不稳定也伴随着时间上的不稳定:我们是在灾难之前还是之后?是在废墟空间内,抑或在孕育之中?
意大利建筑师卡洛·斯卡尔帕曾说:”建筑是建造废墟的艺术。”邦迪似乎字面理解了这句格言:她建造当代废墟,这些空间已内蕴未来分解的痕迹。但这些废墟并不悲怆。它们振动着一种特殊能量,那即是正在进行的变形,缓慢转化材料的化学过程。湿气渗入,铜覆盖绿锈,植物枯萎后再生。房屋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而材料的这种自主生命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艺术家的控制。邦迪坦言:”材料拥有自己的生命。我喜欢说,我设定了条件,知道大致会发生什么,但随后材料自有其所为。”[2]
历史层叠与被遗忘的仪式
如果说居家建筑为Bondi的装置艺术提供了空间框架,那么正是古代历史赋予了她个人神话创作所需的时间深度。艺术家不仅仅是对过去作出引用;她将其召唤、复苏,使之与当下在非线性的时间维度中对话,在这里法老时代的埃及与帝国时代的罗马以及后种族隔离的南非并置。这种历史的多声部从来不是无的放矢:它回应了将艺术实践置于超越当代潮流的长久血统中的需求,并融入文明的延续之中。
在Villa Médicis的驻留加深了她对历史的沉思。罗马凭借其层叠的考古遗迹和建筑见证,为关注生命与死亡循环的艺术家提供了理想的场域。Bondi在此发展了一个”森林再野化”的项目,针对位于罗马法国学院的神秘橡树林Bosco。由保护生物学借用而来的再野化理念在她这里获得了象征意义:这不仅仅是让自然回归其本身,更是重连当代艺术实践与逐渐被遗忘或压制的古老仪式。她重新激活了废弃的蜂巢,安置一座19世纪的祭坛屏风,上面涂覆着信息素和古代香精,证明了她试图构建时代、精神实践与生态之间桥梁的意愿。
她整合进装置中的罗马陶罐不仅是简单的古典象征。它们作为象征性的容器穿越千年,曾先后盛载葡萄酒、油、蜂蜜、香水。这些器皿证明了一个文明对物质、流体、香精的高度重视。Bondi通过创造自身色彩溶液,其时光变幻纵使延续了这种对液态物质的关注。蓝色渐变为淡紫,淡紫趋向深紫色,这种缓慢的色彩变化既唤起古代染料,又带有实验室化学反应的意味。这些色彩盆不仅是单纯的装饰元素:它们是以分子尺度标记时间流逝的生物钟。
古埃及是Bondi作品中的另一重要参照,特别通过苋草的运用。这种植物因其”在古埃及的葬礼仪式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审美属性”而受到她的青睐,体现了仪式实践与当代感知之间的连续性。苋草如泪滴般坠落流淌,创造出植物的忧郁诗意,提醒人们美常在于衰败与凋零之中。通过选择负载历史象征的植物,Bondi拒绝了某些当代艺术实践的消毒中立,完全承担了其作品的精神与宗教维度。
盐,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和人类学意义。自古代以来用于保存食物,作为净化和保护的媒介出现在所有宗教和精神实践中,盐如同一条红线贯穿着各个文明。Bondi 利用这种象征性的普遍性,同时将其与现代的化学特性相结合:氯化钠既是防腐剂,也是具有腐蚀作用、能改变和转化物质的因素。在她的装置作品中,盐从来都不是无辜的;它承载着所有被它保存的肉体的历史,被它消毒的伤口,以及它所缔结的盟约。当她用盐晶树脂覆盖一具鲸骨时,她不仅仅是在展示一个自然过程;她在重新激活一种古老的葬礼仪式,象征大海收回它属于自己的东西。
Bondi的历史观从不学究式,也不冷漠遥远。它体现在具体的动作中:焚烧一个柜子以进行净化,用蜂蜡涂覆一个十字架,将其转化为异教的圣物,种植本地植物以将作品扎根于当地。这些动作属于一种全球人类学的常用仪式,在所有文化中都能看到:火作为转化和再生的媒介,蜂蜡作为蜜蜂生产的神圣物质,植物作为连接生者与死者世界的媒介。Bondi调动这些元素,并不是为体现民俗或异域风情;她是在重新激活一套因现代理性主义而被边缘化、但依然在我们集体潜意识中深刻共鸣的古老知识。
她自童年起所坚持的威卡魔法实践在她的艺术创作中并非无关紧要。她解释道:”我认为正是我的魔法实践让我发现了艺术,艺术随后成为魔法的延伸并接棒了它。但如今,我感受到有将魔法带回艺术中的必要” [3]。如果没有严格的实践和对材料的深入了解,这一声明可能显得天真或挑衅。Bondi并不是玩弄巫术;她将源自精神传统的方法论应用于当代艺术,这些传统赋予物体和物质以行动能力。讽刺的是,这种方法使她与布鲁诺·拉图尔等哲学家提出的”能动对象”理论相呼应,尽管Bondi是通过感性体验而非理论推演走到了这一结论 [4]。
因此,Bondi眼中的历史从不是舞台布景或学识的储备。历史是一种活的、多孔的物质,持续作用于当下。古文明并未消失:它们存在于我们的日常行为中、我们对物件的关系中,以及我们无意识的仪式中。通过将罗马的陶罐与十九世纪的药房柜以及当代植物相互对话,Bondi拒绝了进步的线性观念,提出了一种循环且层叠的时间观,在这里过去与现在共存并相互影响。
走向不稳定的诗学
邦迪让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她装置作品无可否认的美丽,更在于她对完全掌控的拒绝。在一个艺术界常常痴迷于控制和技术完美的世界里,她承认她所发起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对材料的这份谦逊,以及接受作品具有部分超出创作者掌控的自主生命,或许是她对当代艺术最激进的贡献。她无疑继承了意大利贫穷艺术(Arte Povera)对贫瘠材料的关注和让材料自行表达的意愿,但她为此增添了自己独特的时间性和精神层面。在贫穷艺术的艺术家们常用无生命材料时,邦迪更偏爱生机勃勃、有机且挥发性的物质,它们在我们眼前不断变化。
她作品的这种内在不稳定性质质疑了我们对永恒性和保存的关系。在一个传统上重视作品作为可跨越世纪的稳定物件的艺术体系中,邦迪提出了会变化、退化、再生的作品。它们不作为固定的物件存在,更像是进行中的过程,是不断变形质料的过渡状态。这种方法显然给藏家和机构带来实际问题,但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对存在本质的深刻哲学视角:万物流动,一切变化,而试图将生命固定在永久形态是致命的幻觉。
邦迪对本土植物的关注体现了一种不仅停留于话语而体现在实践中的生态意识。她系统地使用当地植物在装置中,使她的作品扎根于其展开的地域,拒绝某些当代艺术实践的抽象普遍主义。每件装置因此成了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庆祝,是对构成世界真实丰富性的特定生态系统的致敬,反对全球化的同质化。这一做法在当下尤为有共鸣,在生态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的时代。
邦迪立于多种传统和影响的交汇点。她的生平轨迹, , 出生于约翰内斯堡,在南非和法国受训,现居意大利, , 使她成为一位拒绝单一归属认同的跨文化艺术家。这种身份的多样性反映在她的作品中,同时召唤非洲、欧洲及普世传统,但从不简化为其中之一。她代表了一代艺术家,他们视国家边界为多孔,构建起基于自觉借鉴和重新诠释的视觉语言。
她与伊娃·尼尔森(Eva Nielsen)、里昂内尔·萨巴泰(Lionel Sabatté)和谢磊一起被提名角逐马塞尔·杜尚奖(Prix Marcel-Duchamp),这标志着她非凡上升的艺术生涯。但超越机构认可,邦迪最重要的是她一贯坚持并历经十余年自我确立的艺术视觉。从2019年里昂双年展呈现的覆盖盐的厨房到2025年巴黎现代美术馆展出的Silent House,我们看到相同的执着:将家庭建筑作为缺席的舞台,有机材料作为转化媒介,古老历史作为象征储藏,精神性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
有人可能会指责Bondi的作品带有一种近乎神秘主义的晦涩,这种指责接近于对蒙昧主义的批评。这是对她方法严谨性和材料处理精准性的误解。她逐渐摆脱与科学家的合作,正是因为科学术语和实验方法不符合她直觉式理解化学过程的方式。但这种直觉并非无知:它源于多年积累的感性认识,对盐、蜡和植物的行为有着亲密的熟悉。这里可以称之为一种本土科学,一种不依赖学术规范但在应用中同样严谨的工艺技巧。
Bondi关注的世界再魔法化问题,并非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神话黄金时代的倒退怀旧。她更是在承认,尽管现代工具理性带来了不可否认的益处,却也使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变得贫乏,将物品简化为其单纯的使用价值。给日常物品重新赋予魔力,就是还原其象征深度,使其承载超越即时功能的意义。一只橱柜不仅仅是一只橱柜:它还是存放曾接触过我们肌肤的衣物的容器,是积聚其间气味的地方,是藏匿秘密的所在。Bondi提醒我们这个我们常常忘记的显而易见的事实。
经过对Bianca Bondi作品的梳理后,明显可见:我们面对的是一位重要的艺术家,她的创作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展开并带来惊喜。她的装置作品Silent House并非终点,而是在不断深入研究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静默之屋却有力地诉说着我们当代的处境:我们居住的地方将超越我们的存在,我们操作的物件将铭刻我们的痕迹,我们属于一条超越我们并早已存在的历史链条。面对这种对有限性的深刻意识,Bondi既不提供轻易的安慰,也不纵容绝望。她仅邀请我们细心观察周围缓慢的变迁,接受不稳定作为存在的基本条件,并庆祝从变化与腐朽过程散发出的矛盾之美。或许,这正是她作品的深层意义:教我们将废墟视为一种承诺,而非终结,那是一种在废墟中可能实现的再生。在一个以令人不安的速度走向自我毁灭的世界中,这样的谦逊与韧性的教诲尤为迫切。
- 蓬皮杜中心,”当魔法遇见艺术:Bianca Bondi迷人宇宙”,Pompidou+,2025年。
- Art Basel,”马塞尔·杜尚奖2025:Bianca Bondi”,2025年9月。
- 同上。
- CRAC Occitanie,”Alexandra Bircken & Bianca Bondi展览”,塞特,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