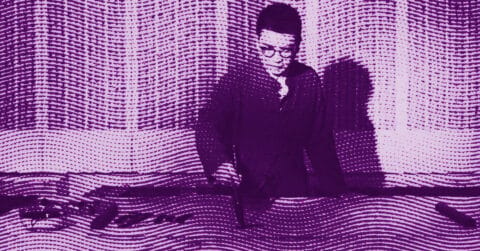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Marlene Dumas 不仅仅画肖像,她以应有的外科精确度剖析人类灵魂,这足以让你整夜难眠。她于1953年出生于开普敦,自1976年起定居阿姆斯特丹,构建了一个始终拒绝让我们在审美上自我满足的作品体系。在你们寻找美的地方,她呈现给你们的是事实,亲爱的朋友们,事实从来都不是赏心悦目的。
这位艺术家以二手图像为媒介,如杂志照片、色情快照或朋友的宝丽来照片,并将它们进行彻底的变形。她流动般的笔触、湿画法及不寻常的色彩,创造出似乎在眼前逐渐消融的面容。这些形象不代表个体,而是情绪状态、心理紧张、被压抑的暴力。这正是Dumas区别于当代肖像画家的地方:她不试图捕捉相似性,而是揭示隐藏在人类表面之下的涌动。
她与波德莱尔诗歌的关联值得深入探讨,因为这为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提供了特别清晰的阐释。2021年,奥赛博物馆庆祝查尔斯·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邀请Dumas 创作一系列受《巴黎的忧郁》[1]启发的作品。这次两个同样热爱恐怖之美的精神的逝世后合作绝非偶然。波德莱尔,这位看到现代性中辉煌与苦难不可分割混合的诗人,在Dumas身上找到了精神上的继承者,她与他一样痴迷于美的矛盾。
这项目诞生的十四幅画作展示了Dumas艺术的巅峰,她在诗人与其情妇让娜·迪瓦尔的精确肖像以及源自诗歌的抽象图案(老鼠、瓶子、穷人的玩具)之间游刃有余。正如波德莱尔在他的散文诗中描述社会在进步与颓废间的悖论,Dumas 绘制了一个同时承载天真与残酷的人类矛盾。艺术家本人曾坦言这项工作的艰难,努力”画出一个人的肖像,在其脸上展现这一切的某种东西”,面对波德莱尔文本中”矛盾情绪与诗意跳跃”[2]。
这位《恶之花》诗人与她的亲近关系根植于对艺术作为揭示令人不安真理的共同视角。波德莱尔谴责”无所事事的女士和自称绅士们的愚蠢与虚荣”,Dumas 拆解每一幅画背后的权力机制。她受《巴黎的忧郁》启发的画作不仅是简单的插图,而是对诗人对现代人类状况疑问的视觉回应。她画了两次波德莱尔的面容,形象幽灵般,几乎消逝,仿佛诗人从彼岸继续以无情的目光审视我们的集体灵魂。
为奥赛博物馆创作的系列作品特别探讨了穿越波德莱尔作品的孤独与绝望主题。在《老妇人的绝望》中,Dumas 描绘了一位几乎被黑色颜料完全覆盖、蜷缩在角落里的女性,这一形象表现出一种如此绝对的痛苦,以至于几乎抽象化。这种将诗歌情感浓缩为纯视觉感受的能力使 Dumas 靠近波德莱尔的美学,其中丑与美、崇高与卑劣在一种富有张力的生产性紧张中共存。诗人曾写道艺术应当从恶中提取美;而 Dumas 则断言”如果不展示生活恐怖的一部分,就没有美”[3]。
与波德莱尔的这种契合也揭示了文学在 Dumas 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她的作品汲取了”激情且片段式”的诗歌和文学阅读。她不寻求去阐释文本,而是建立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让绘画与文字相互丰富。她的画作因而成为回荡着其他声音、其他时代回声的空间,创造出一种多声部合唱,拒绝单纯的观看,要求观众的智力与情感投入。
她作品中的精神分析维度构成了其艺术方法的第二个支柱,Dumas 在1978年至1980年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学习心理学并非巧合。这段学习经历深刻影响了她对肖像的处理,她更将肖像视为无意识领域的地图,而非单纯的物理呈现。她的画作如同分析会话,潜意识中的压抑浮现,社会面具破裂,显露出我们更愿意隐藏的部分。
Dumas 特别关注人类心灵的模糊地带:性以其最原始的表现形式、潜伏于每个人内在的暴力、源自压迫社会结构的罪恶感。她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童年滋养了她对统治与排斥心理机制的持续思考。诸如《邪恶是平庸的》(1984) 等作品中,她描绘自己拥有被熏黑的脸和手,质问作为一名白人女性在种族主义体系中的共谋身份。她能够将分析手术刀反向对准自己,展示了罕见的知识诚实。
性别认同和欲望表达的问题也以特别的强度贯穿她的作品。Dumas 所绘裸像完全摒弃传统的情色意味,展现的是暴露于脆弱、陌生感及威胁潜能中的身体。她常以色情材料为素材,将其改造为介于揭示与隐匿、暴露与羞涩之间的图像。这种模棱两可反映了人类性欲固有的紧张关系,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意识核心中冲动与压抑的混合。
她对儿童的肖像,特别是自己女儿 Helena 的肖像,以拒绝煽情著称。她描绘的婴儿常显绿意,几乎带有怪物特征,如《Die Baba》(1985)中那个面貌似希特勒的孩子,提出了令人难以承受的问题:无辜何时转变为残酷?这些形象挑战了我们将童年视为恩典状态的需求,迫使我们承认暴力与破坏性也是人类状况从最幼年开始即存在的组成部分。
杜马斯与其作为原始素材所使用的摄影图像之间的关系,同样展现了她对投射与认同心理机制的敏锐理解。她从不卑躬屈膝地复制她的来源材料,而是对其进行一种疏离处理,让艺术家的无意识渗透到表现中。这种方法呼应了关于幻想屏幕的理论,那是一种投射我们欲望和焦虑的表面。她所绘的面孔因此成为扭曲的镜子,让我们在其中认出一些自身的东西,甚至,尤其是在图像令我们厌恶的时候。
系列《Models》(1994)或娜奥米·坎贝尔(1995)的肖像通过他者的视角质问身份建构的机制。在描绘这些美的偶像时,杜马斯并非歌颂她们的魅力,而是揭示了将她们构成男性欲望对象的象征暴力。她那液态的笔触使面孔字面上流淌着,仿佛身份本身只是一种脆弱的建构,总是面临解体的威胁。这种自我形象的根本不稳定性深刻呼应了精神分析关于主体本质上是分裂的、碎片化的并且不断重构的观点。
她对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肖像,例如奥萨马·本·拉登(2010年)的作品,进一步推动了对集体潜意识阴影区域的探讨。通过将恐怖分子人性化,杜马斯并非赞美暴力,而是让我们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怪物与我们相似。她拒绝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探索即使在最令人厌恶的人物中依然存在的共同人性,这种能力展现出超越单纯绘画练习的深刻分析力。
视线与认可的问题,在关于主体形成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贯穿杜马斯的整个作品。她的形象常常以令人不安的强烈目光注视着我们,使我们成为同谋的窥视者。这种”看见与被看见”的游戏,这种构成主体同时又威胁主体的视线辩证结构,塑造了杜马斯在作品与观者之间建立的关系。我们无法被动地凝视她的画作,它们牵涉我们、指责我们,迫使我们承认自己在她所表现的权力与欲望结构中的参与。
杜马斯对身体表现的创作,无论是裸体、肖像还是情色场景,始终拒绝理想化。她的角色承载着他们心理历史的烙印:苦恼可以从面部特征的扭曲中读出,暴力体现在厚重的绘画质感中,欲望则藏在超出轮廓流淌开来的色彩流动中。绘画的这种物质性本身成为对身体物质性及其所居无意识的探讨载体。
她的湿对湿技法,使颜色相互融合、互相渗透,象征了心理过程本身。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一切流动、变化、逃离掌控。影像的这种流动性反映了精神分析所理解的无意识的流动特性:一个持续的联想、浓缩、位移的流动,抵抗任何最终固定的尝试。
她承认受到爱德华·蒙克或弗朗西斯·培根等艺术家的影响,这并非偶然。这些画家与她共享对精神痛苦视觉表现的执着,关注那些内心世界溢出表象并扭曲可见之物的时刻。但当培根将她的形象囚禁在建筑牢笼中,蒙克把它们置于表现主义景观时,杜马斯更喜欢将她们孤立于中性背景上,将所有的情感强度集中在面孔和身体的处理上。
她整个作品中令人震撼的是对安慰的绝对拒绝。杜马斯不给我们任何慰藉,也不给我们面对她揭示的真相时的逃避通道。她的画作以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症状方式运作:它们揭示了本应隐藏的东西,体现了被压抑内容以伪装但可识别的形式回归。她艺术中这种症状性维度也许解释了为何其作品常引发不适,我们面对的是那些我们宁愿忽视的自我和社会面向。
当我们接近这段思考的尾声时,玛琳·杜马斯的作品显现出它挑战任何便捷分类的特质。她既非单纯的肖像画家,亦非表现主义者,更非新浪漫主义者,她是这些身份的结合体,却又完全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她的艺术如同破碎的镜子,映照出无法重组成和谐整体的真理碎片。这种碎片化或许也是她最宝贵的贡献:在一个充斥着光滑影像和程式化表达的时代,杜马斯提醒我们,人类本质上是不可复制、不可简化和不可捉摸的。
她能够在同一创作路径中融合欧洲伟大诗歌的遗产和精神分析思想对人类心灵深处的直觉,这使她不仅仅是一个当代艺术家。她自居为灵魂的考古学家,内心领土的制图师,那些我们不敢探索的领域。她的画作不只是装饰墙壁,而是穿透墙壁,开辟了令人眩晕的裂缝,通往我们宁愿避看的深渊。
2021年,奥赛博物馆给予她的荣誉, , 使她成为第一位在印象派画廊展览的在世艺术家, , 隐含承认了她那非凡的地位。但超越制度性赞誉,她作品所激起的不适感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因为仅带来愉悦的艺术不过是娱乐;只有深刻扰动我们的艺术才值得我们驻足。玛琳·杜马斯创作不是为了取悦,而是为了唤醒、干扰,迫使我们思考和感受那些我们想要逃避的东西。
在这个图像泛滥至无意义,一切都在网速般的速度里消费与遗忘的时代,杜马斯的作品提醒我们,某些图像会抵抗,会坚持,会不断回来纠缠我们。她的肖像正是那种无法忘怀的肖像,正因为它们无法让我们平静。它们在我们离开后长久地在内心运作,如同扎入意识的刺,如同无解问题在梦境中追随我们。
这最终是伟大艺术的标志:不是它当时令我们惊叹,任何精心制作的表演都能做到这一点,而是它继续在我们内心运作,改变我们对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看法。Marlene Dumas 确实画了面孔,但这样做,她重塑了我们的面孔。她迫使我们以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方式看待自己,正因如此,当许多其他作品被遗忘时,她的作品将依然存在。她说,美不存在于不展示生活的恐怖之中。而我们,作为自己衰败的无奈观众,只有对她那些递给我们的无情镜子的画作默然点头:是的,正是我们,以我们全部的凄美辉煌,被你们描绘出来了。
- 展览”Marlene Dumas : Le Spleen de Paris”,奥赛博物馆,巴黎,2021年10月12日 – 2022年1月30日,该项目与 Donatien Grau 合作设计
- 与 Marlene Dumas 的访谈,Artnet News,2021年11月
- Marlene Dumas,《Sweet Nothings: Notes and Texts, 1982-2014》,D.A.P.,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