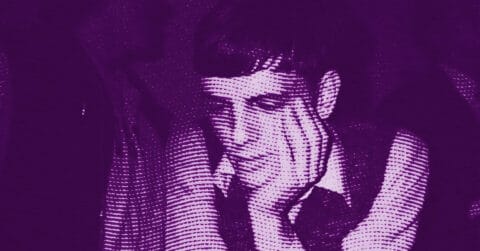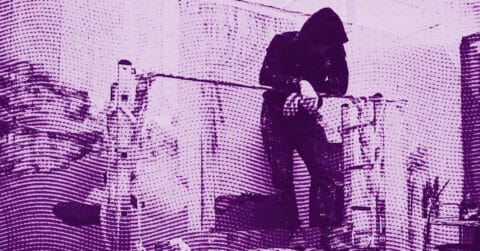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尼克·布兰特,1964 年出生于伦敦,不只是简单一名从空调四驱车里用长焦镜头拍摄斑马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他是我们时代的泰奥多尔·热里柯,不是定格《梅杜莎之筏》,而是定格我们自然世界的最终沉没。如果你认为这种比较言过其实,那说明你根本不懂他作品的力量。
让我们从他对野生动物摄影的革命性方式说起。当大多数野生动物摄影师躲在庞大的长焦镜头后捕捉壮观的动作镜头时,布兰特却完全相反。他带着一台简单的 Pentax 67II 和定焦镜头,像拍摄工作室肖像一样接近拍摄对象。
他的技巧大胆得几近疯狂。试想一下,用一台中画幅相机,在几米之外拍摄一只狮子,而每次按下快门时都发出像电钻一样的响声,那意味着什么。这不只是摄影,这是审美上的俄罗斯轮盘赌。但正是这种身体上的接近,赋予了他的影像以形而上学的力量。当你观看他那黑白的大象肖像时,你不仅仅看到的是厚皮动物,而是面对着有意识的生命,它们凝视着你,即将走向灭绝的边缘。
他使用黑白的方式堪称大师级。这并不是为了制造”艺术感”而作出的审美上容易的选择,诸多平庸的摄影师常常这样做。不,他的黑白铿锵如剃刀之刃。他剥去画面的所有色彩干扰,迫使我们看到最本质的东西:这些生物的纯粹存在,它们与生俱来的尊严及绝对的脆弱。这正是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所说的”他者的面容”,这种存在向我们施加了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
在他的系列《On This Earth》中,Brandt向我们展示了似乎已成幽灵的动物。斑马如迷雾中的幽灵般浮现,是逐渐消失的过去的幽魂。长颈鹿在天空中轮廓分明,如同我们正在遗忘的象形文字。每一帧影像都是一首视觉颂歌,是对人类世的死亡提醒。这种手法让人联想到贝恩特和希拉·贝乔尔对工业结构的研究,但Brandt并非在记录工业革命的遗迹,而是在编录这场革命的受害者。
但真正令他作品达到先知般境界的是《This Empty World》系列。这个系列对我们的集体意识是一记重拳。Brandt在大草原上建造巨大场景, , 加油站、建筑工地、道路, , 制造自然世界与工业文明间的视觉碰撞,让《银翼杀手》如同一部浪漫喜剧。技术手法令人震惊:他安装带运动传感器的摄像机,等待数月让动物适应这些结构,然后完善场景,添加人类元素。结果是具有前所未有的象征暴力。
看这张图,一头大象迷失于夜晚的建筑工地。工人们沉浸于手机,完全忽视了这尊雄伟的生命。人造光线营造出梦魇般的氛围,让人想起霍普尔的画作,但这里演绎的不是城市孤寂,而是环境异化。大象变成了一座巨型的死亡警示,提醒我们在对”进步”的疯狂追逐中,正在失去什么。
这个系列呼应了人类学家安娜·青关于”资本主义废墟”的理论。但Brandt更进一步:他不仅纪录这些废墟,还创造出视觉寓言,迫使我们直面自身的野蛮。每一幅画面都是指控、预言与哀叹。
“横跨荒芜之地”系列进一步探讨了我们毁灭能力的反思。守护者手持偷猎象牙防御的画面充满了悲剧力量,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哀悼像。但取代圣母怀抱着她儿子的尸体的,是人们手持被屠杀的生物残骸,以满足人类的虚荣。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会称之为”辩证图像”,这种图像揭示了我们文明的根本矛盾。
纳特龙湖石化动物的肖像可能是该系列中最令人不安的图像。这些被钙化的生物,凝固在令人联想到庞贝模具的姿势中,成为我们集体冷漠的纪念碑。这是杰里科与乔尔-彼得·维特金的结合,崇高与恐怖在同一画面中融合。
通过”破晓之日”,布兰特将他的艺术提升到了新的概念复杂程度。这个描绘人类与动物在雾中的肖像系列,他们都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美得令人难以承受。笼罩着其主题的人工雾气不仅是简单的美学效果,而是我们集体盲目状态的视觉隐喻。每幅图像都构建得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精心注意构图和光线,但信息却是坚定的当代性。
这些肖像配以令人心碎的见证:因干旱失去土地的农民、因灾难性洪水被迫离开家园的家庭、岌岌可危幸免于灭绝的动物。这正是哲学家雅克·郎西埃所称的”感知的分享”,是对我们社会中可见与可言说事物的一次再分配。布兰特赋予那些在气候变化话语中通常隐形的人以声音和面孔。
他最新的系列”SINK / RISE”,在斐济拍摄,或许是迄今为止他最大胆的作品。这些在水下拍摄的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岛民肖像充满了刺骨的讽刺。主体们在进行日常活动, , 坐在沙发上、站在椅子上,但却在水下。这是魔幻现实主义与环境纪录片的结合。这些图像让人想起比尔·维奥拉的装置艺术,但不是探讨精神性,而是直面气候变化的残酷现实。
“我们的声音回响”这一最新系列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它如何将气候危机与难民危机联系起来。透过在约旦拍摄的叙利亚家庭(这是全球第二个最严重缺水的国家),布兰特展示了环境灾难与人道危机的密不可分。高高堆放着箱子的家庭肖像直冲云霄,象征力量非凡,展现出既脆弱又坚韧的垂直性。
布兰特的技艺严谨,他的视角无情。为了《这个空荡荡的世界》,他开发了复杂的流程,涉及精细的照明系统、运动传感器和宏大的布景。每幅图像都经历了数月的准备和等待。这种修道院般的耐心让人想起十九世纪的伟大摄影师,但服务于当代迫切的现实。
一些评论家将他的作品简化为”保护摄影”或”环境新闻摄影”。这是多么荒谬!布兰特是一位概念艺术家,他以摄影作为媒介,创造了一种关于人类世的新视觉神话。他的图像不是文件,而是愿景、预言、视觉宣言。
他在夜景中使用人造光的方式尤为引人注目。这些生硬的灯光让人联想到乔治·德·拉图尔的画作,营造出一种末日剧场的氛围。投射的阴影与主体同等重要,创造了复杂的视觉编舞,令人联想到皮拉内西的蚀刻作品。
布兰特与许多当代摄影师的区别在于他对犬儒主义的绝对拒绝。在一个讽刺已成默认姿态的艺术世界里,他敢于真诚到底。他的愤怒是真实的,他的同情是真实的,他的绝望是真实的。这正是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所称的”投入”,一种不仅反映世界而且试图改变世界的艺术。
他与大生命基金会(Big Life Foundation)的合作表明,他不仅仅是在记录破坏,他实际行动起来抗击破坏。这种艺术与激进主义的融合让人想起20世纪初的先锋派,但紧迫感更加强烈。因为不同于想改变生活的超现实主义者,布兰特实际上是在为保护生命而斗争。
他处理时间性的方式令人着迷。他的摄影作品似乎同时存在于多个时间层面:它们记录当下,预言未来,哀悼过去。这正是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所称的”存续”,即某些图像携带着古老形态的记忆。
在技术上,他从胶片转向数字摄影,拍摄《这空旷的世界》及其后续作品,并未削弱他视野的力量。如果说他早期的黑白影像让人联想到19世纪的摄影作品,那他近期的彩色作品则创造了自己的视觉语言。他夜景中饱和的色彩与我们当前对自然的人工化关系一样人工。
对于那些仍认为摄影只是简单记录的人来说,布兰特的作品是一记极具警示意义的耳光。他的图像是复杂的构造,需如同历史画一样进行精心策划和深思熟虑。区别在于他描绘的历史正在我们眼前展开,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共同参与者。
他对布景的运用丝毫不减其作品的真实性。相反,正如沃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有时候虚构是通向真理的最佳途径。布兰特构建的场景揭示了比任何传统纪录片更深刻的真理。
尼克·布兰特的作品是对我们集体死亡的严厉提醒。他的图像迫使我们正视通常选择忽视的事情:我们对自然世界毁灭负有责任。如果你不理解他作品的重要性,那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他的作品不是为了安慰或娱乐我们,而是为了在为时已晚之前唤醒我们摆脱消费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