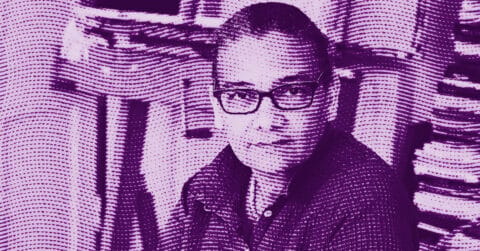请认真听我说,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人:当代艺术中有一位年轻的利比亚女艺术家,她拒绝轻易的确定性,宁愿在纺织与建筑、记忆与流动交汇的缝隙中编织她的语言。Nour Jaouda,生于1997年,在伦敦和开罗之间工作,创作挂毯及装置,锐利地质询地点、身份与灵性概念。她的作品曾于2024年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展出,现于斯派克岛(布里斯托尔)展至2026年1月,提出了在持续移动状态下居住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
诗歌作为流亡的地图学
Jaouda 的作品深植于巴勒斯坦诗人 Mahmoud Darwish 的诗歌。她在威尼斯展出的三件挂毯,直接受 Darwish 擬人化橄榄树的启发,这种树象征根基与流离。Darwish 从流亡立场书写,寻求诗意语言中的流动故乡。Jaouda 用纺织做同样的事,创造她所称的 “存在于临界空间的记忆景观”。她在班加西祖母家的无花果树意象,在Where the fig tree cannot be fenced(2023)中具象化,这延续了对树作为不可能归属隐喻的思考。植物形态被解构至几乎难以辨认,凝聚于层叠的绿色景观,空缺处作为诗意的静默。
引人注目的是 Jaouda 如何将诗歌语法转译成纺织词汇。每一次剪裁、组装、染色皆是具象隐喻。她引用的后殖民理论家 Edward Said 和 Stuart Hall 解析文化身份是流动而非固定。Jaouda 采纳此理论,却将其转化为感知领域,创作的作品字面上体现了这个”成为”的过程。她的纺织品不代表身份,而是身份的表演。
黎巴嫩作家 Etel Adnan 的一句话被 Jaouda 引用:”地理地点成为精神概念” [1],提供了另一锚点。Adnan 也在多语言多地理间生活,理解流动不仅是身体的,更是本体的。地点成为概念,地图成为冥想。Dust that never settles(2024),以洋蓝与渗融的绿色具象化了地理拒绝定格的理念。染色过程缓慢,植物染料渗透布料需24小时,干燥再需24小时,强制了一种近似诗歌写作的冥想时序。每一道折痕携带旅行箱,成为作品的有形组成,是旅途的物质铭刻,流离的触觉档案。
建筑作为神圣的门槛
如果说诗歌提供了概念框架,那么正是建筑形式上结构化了Jaouda的作品。她对埃及建筑师AbdelWahed El-Wakil的兴趣并非偶然,后者以其对本土建筑和神圣几何的运用而闻名。El-Wakil主张建筑不必是永久性的。这一理念在Jaouda的实践中得到了直接的呼应,对她来说,纺织品可以卷起、搬运,并重新安装到新的环境中。
装置作品Before the Last Sky(2025年),于伊斯兰艺术双年展上展出,是这一方法的一个范例。该作品包括三幅悬挂于天花板并垂至地面的幅员宽大的织锦,描绘了伊斯兰祷告的姿势:sujud、ruqu’和julus。这些纺织品悬挂在被解构的金属门框上,创造了一种视角的逆转:门从天空降临,而非从地面升起。安装作品采用了伊斯兰城垛的图案,这些建筑装饰性形状位于清真寺顶端。城垛吸引了Jaouda,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临界空间,在实与虚、地与天、物质与精神之间交替。她聚焦于城垛之间的负空间,从缺失中创造意义。这种手法展现了对伊斯兰美学的深刻理解,避免了具象表现,通过几何的重复表达神圣。
祈祷垫作为Jaouda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形态,构成了她的典范建筑。这块普通纺织品通过祷告行为成为神圣空间。它创造了一个临时的”第三空间”,一个可以在任何地方展开的门槛。这种神圣的可携带性与艺术家因生活经历而具备的流动性相呼应。她所使用的钢结构, , 来自开罗市场回收的门框和拱门, , 作为建筑骨架,不阻断空间,邀请观众围绕及穿越。2024年巴塞尔艺术展上的The Shadow of every tree,Jaouda构建了一个宽大的钢门,横跨整个展览空间,迫使访客跨越这道门槛。该门拒绝了直接通行,但又邀请探索。
她对组织空间而不隔断空间结构的关注让人联想到moucharabieh, , 这些镂空的木制窗格使人既能看见外面,又难被看到。Jaouda的纺织品亦有类似作用:塑造空间却保持渗透性。2025年于Spike Island展出的装置The iris grows on both sides of the fence,与开罗Chariah-el-Khayamia工匠合作设计成帐篷,营造了一个为被根除的风景哀悼的集体场所。选择以巴勒斯坦国花Faqqoa鸢尾花装饰此帐篷绝非偶然。这种花,象征抵抗和希望,生长在围栏的两侧。Jaouda的纺织建筑拒绝二元分割:它创造了多重故事、多重地理共存的空间。她的作品既非绘画亦非雕塑,居于二者之间,拒绝僵化的分类。
过程即哲学
Jaouda 的创作过程在哲学上体现了她的愿景。她开始勾勒出她遇到的几何和有机形状:开罗清真寺的格子结构、花卉图案、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元素。这些平面形状被转化为她剪裁、塑形、撕裂、重构和缝合的物件。她使用的词汇具有启示性:”解构”、”破坏”、”剥离”。这种通过解构来构建的矛盾方法,在她提到的后殖民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证明。霍尔和赛义德已经表明,文化身份通过流动而形成。
植物染色这一缓慢且不可预测的过程赋予了颜料独特的能动性。颜色渗入纤维,改变了织物的物质性。在开罗,她的作品呈现出温暖的黄色和深邃的蓝色;在伦敦,颜色变得冷却,呈现出含蓄的绿色、棕色和紫色。颜色成为超越语言的表达。这种游牧式的实践在作品中物理地记录了迁移。Jaouda 断言这种”无根存在”[2] 是她研究的核心。她的作品具备一种罕见的品质,同时完整且未完成。这种不确定性反映了艺术家对文化身份是”一种不断成为的过程”[3]的信念。织物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们参与了一种超越单一对象的连续性。
居住于两者之间
在这次探索的结尾,应记住什么?Jaouda 的作品抗拒简化,拒绝明确的归属,培养一种富有成效的模糊性。她的概念方法与物质实现之间的连贯性令人印象深刻:流动性不是她阐释的主题,而是她实践的前提。能够折叠、携带、重新安置的纺织品字面上体现了可携带身份的理念。祷告垫在放置之处创造神圣空间,成为携带自身地点与历史可能性的隐喻。
在一个移民流动日益加剧,数百万人生活在多个国家、多种语言、多样文化之间的世界,Jaouda 的作品为理解这种状态提供了一个范例,将其视为财富而非缺陷,是同时居住于多个世界的能力。精神维度值得强调。在当代艺术界常对宗教话题持排斥态度的环境中,Jaouda 坚定地承担这一维度而不陷入宗教式的插图。她对伊斯兰祈祷和神圣空间的关注,不是防御性身份认同的表现,而是对构成神圣之地的真诚探问。
她作品的诗意品质,即将复杂现实浓缩于唤起联想而非描述性的形式的能力,使其区别于偏重话语而轻视感官经验的某些概念艺术。Jaouda 的纺织作品在多个层面上运作:它们可因其形式之美、华丽色彩而被欣赏;但对愿意放慢脚步的人而言,它们也能提供更深层的解读。这种多义性是一种力量。将这件作品简单视为对当代地缘政治危机的反应是诱人的,但也是对其的简化。当然,巴勒斯坦鸢尾花的出现,引用赛义德的标题Before the Last Sky,以及对班加西无花果树的提及,将作品植根于悲剧现实。但 Jaouda 拒绝艺术作为政治的直接插图。她在更细腻的层面操作,创造一种美与哀悼共存的空间。
使她的作品变得必要的是她保持复杂性的能力,抵制二元简化。在一个言论滋生于截然分裂的时代,我们与他们,这边与那边,Jaouda 提出故意居于中间空间的形式。她的纺织品既非东方也非西方,既非传统也非当代。它们存在于那个”非此非彼”的空间中,这也是一个”既此又彼”,确认多重归属的可能性。Jaouda 的作品提醒我们,艺术的使命不是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保持基本问题的开放。生活在多个世界之间,归属某地意味着什么?如何携带自己的文化而不将其定格为民俗?如何创造圣洁?如何通过解构来建构?
这些疑问贯穿她的纺织品,却从未以舒适的确定性解决。正是这种富有成效的张力,这种根植与去根、存在与缺席、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微妙平衡,构成她作品的力量。在一个即将被迁徙主导的世纪里,关于拥有或失去归属地的意义将变得愈加尖锐,Jaouda 的作品不仅是一种美学思考。它提出了一种存在方式,一种调和流动性和归属需求的生活方式。她的纺织品不是被动观赏的物件,而是存在的提案,是重新思考我们与地点、身份、圣洁关系的邀请。这就是为什么 Nour Jaouda 是她那代人中最重要的艺术声音之一。
- Etel Adnan, Journey to Mount Tamalpais, The Post-Apollo Press, 1986
- Sofia Hallström, “Artist Nour Jaouda’s landscapes of memory”, Art Basel, 2024年3月
- Lu Rose Cunningham, “In Conversation with Nour Jaouda”, L’Essenziale Studio Vol.08, 2025年4月